曾幾何時,阿以衝突、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定居點、隔離牆、路線圖等名詞不僅已成為各國政要和外交官員們的口頭語,而且也成為世界各地新聞媒體報導的關鍵字,甚至成為尋常百姓們飯後茶余的談資。全世界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關注著巴勒斯坦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
雖然,現代人類都聚集在一個天涯共此時的瞭望臺上,但由於彼此迥異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考量使得人們對同一個問題的見解和判斷呈紛紜之勢,不過,在聚訟繁復的表像下,阿拉伯、美國和以色列等各自的觀點和立場無疑成為三種主要的話語形態。但遺憾的是,美國與以色列作為利益共同體早已達成對付阿拉伯人的戰略默契。以致長期以來,懸殊的實力和失衡的格局一度使阿以之間從未展開過勢均力敵的較量。關注阿以局勢的人都知道,面對全副武裝的以色列部隊的挑釁和炫耀,更面對生化武器的威脅和傷害,巴勒斯坦穆斯林唯一的力量就是平民和手中的石頭。他們唯一的願望就是看到家園的和平和寧靜,但以色列和美國人也在呼籲和平,其實圍繞這個貌似共同的目標,各自打著不同的算盤。
大半個世紀以來,在美國的支持和援助下,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這片土地上,施展渾身解數,盡情表演——侵略、流放、羈押、隔離、暗殺、擴張定居點、沒收土地、查抄財產、水中投毒、傳播霍亂、實施細菌戰等各種恐怖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復國計畫,公然挑戰國際法規,悍然侵犯人權公約和正義原則,其累累罪行和斑斑汙跡,若以編年史計,則馨竹難書。
巴勒斯坦問題,不僅是兩個國家和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而且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從中漁利的問題。對以色列人而言,他們的問題就是猶太復國計畫如何儘快實現,對美國人而言,其問題就是插足阿以衝突,控制局勢,獨霸中東,對阿拉伯人而言,他們的問題就是流離失所的親人何時能夠重返家園,久違的和平何時再能成為現實。彼此的夢想針鋒相對,形同水火,坐下來想談也找不到共同的話語基礎,只能誰強誰說了算,戰爭的邏輯遂演繹為叢林的法則。至於什麼海牙公約、日內瓦公約、安理會決議和聯大決議以及和平路線圖都為美國的雙重標準所綁架,甚至淪為為其服務的政治工具。以色列的哪一樁罪行、哪一次恐怖事件沒有觸犯過上述冠冕堂皇的法規和慣例,誰見過以色列聽命伏法、有所收斂,而不是肆無忌憚、有恃無恐。如果是阿拉伯人不慎違反了其中的任何一條法規,那麼,美國就會以反恐或維權的名義去合法的殺人。
戰爭是美國和以色列一手導演並付諸實施的,一旦戰爭的成本超過了利益估算和戰略考量時,和平似乎又成為坐下來對話的契機。然而遺憾的是,這種機會又在美國和以色列缺乏誠意甚至心懷叵測的扯皮中稍縱即逝,和平進程又一次從公眾視野中被放逐,路線圖再一次形同虛設。在以色列人的意識中,猶太復國計畫甚於摩西十誡或聖經托拉,至於人世間的公理、道義和秩序以及國際社會共循的法規、準則和慣例則相比之下可以忽略不計。於是,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穆斯林的生命和財產理所當然的成為其復國計畫的殉葬品,正如以色列教育部副部長說的,我們殺害巴勒斯坦兒童是無可厚非的。真不敢相信,一個比法西斯還殘忍的人,竟忝列教育行列並執其牛耳。其實對於把陰謀和野心當做信仰的以色列人而言,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比如說忘恩負義。
早在西元四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剛皈依基督教不久的君士坦丁大帝就發佈了各種歧視猶太人的政令——猶太人不得改信其它宗教,不得與基督徒通婚,不得與基督徒共餐,不准建造新的猶太教堂,禁止從事醫療工作之類的職業,禁止在訴訟中出庭作證。直至西元十一世紀,在十字軍東征時期,有數萬歐洲猶太人被歐洲基督教徒殺害。西元十三世紀,教皇英諾森頒佈了反猶教令,無數的歐洲猶太人被殺,財產被沒收。歐洲黑死病期間,教會宣佈這場瘟疫是猶太人引起的,於是有許多猶太居住區被燒毀,數千人被殺。西元十九世紀,俄國也掀起了屠殺猶太人的浪潮,歐洲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到了二十世紀達到高潮。二戰期間,光德國納粹就殺害了600多萬猶太人。
然而,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流散在阿拉伯地區的猶太人享受到了信仰、職業、居住和婚姻等方面的保障和自由,西元十二世紀,在安達盧西亞(伊斯蘭文化之都)居住著許多猶太人,辦有多所神學院,有許多猶太哲學家、數學家、語言學家、醫學家和宗教學家都在這裡找到了發揮所學,展露才華的舞臺,而後來在基督教統治西班牙的三個世紀裡,有四十萬猶太人被基督教的宗教裁判所審訊,其中三萬人被處死。
到了十五世紀,費迪南國王下令將全部猶太人逐出西班牙。穆斯林對猶太人的禮遇、優待和保護從西元七世紀穆阿維葉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二戰後期。在穆阿維葉時代,有許多猶太人在穆斯林政府中任職,也有不少猶太人甚至是朝中重要的文臣和武將。1941年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宗教領袖們向各自區域的穆斯林大眾頒佈了不准參與掠奪猶太人財產;不准接受納粹傀儡政權的任何獎賞的教法判決。當時納粹統治北非,傀儡政權對阿爾及利亞穆斯林許諾,只要他們侵奪猶太人的財產,就可以獲得豐厚的獎賞,這種卑鄙的手段在現在以自由、香水和浪漫著稱的法國人那裡獲得了空前成功,但是在阿爾及利亞,因為發自信仰與人道主義的正義立場,沒有一個穆斯林苟且回應。
然而在1948年前後,就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統治者、烏萊瑪及廣大民眾基於人道主義精神和正義原則,全力以赴的保護猶太人的時候,猶太人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土地上忘恩負義地實施其復國的陰謀計畫。從那時起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猶太人絲毫沒有放鬆過對巴勒斯坦穆斯林的迫害、流放、制裁和殺戮。遠寺周圍的襲擾、封鎖和圍困從未間斷,加沙上空的硝煙和炮聲不絕如縷,東耶路撒冷的領土上的大肆擴張;約旦河西岸的隔離牆和定居點像肆虐的洪水勢不可遏,而由此導致上百萬阿拉伯穆斯林家破人亡,淪為難民。對於曾經在歷史上在基督教世界的屠刀下給予其保護和優待的善良的阿拉伯人報之以人世間最殘忍的毀滅性打擊,對此慘絕人寰的反人道主義悲劇,以色列人沒有絲毫的負罪感和愧疚感。
那個武裝到牙齒的毒蛇,以復國的名義狐假虎威的盤踞在世代崇尚正義與和平的土地上,善良的阿拉伯穆斯林除了流浪和抗爭,只能翹首和平,期盼還鄉,與失散的親人再度聚首。
【轉自《我們》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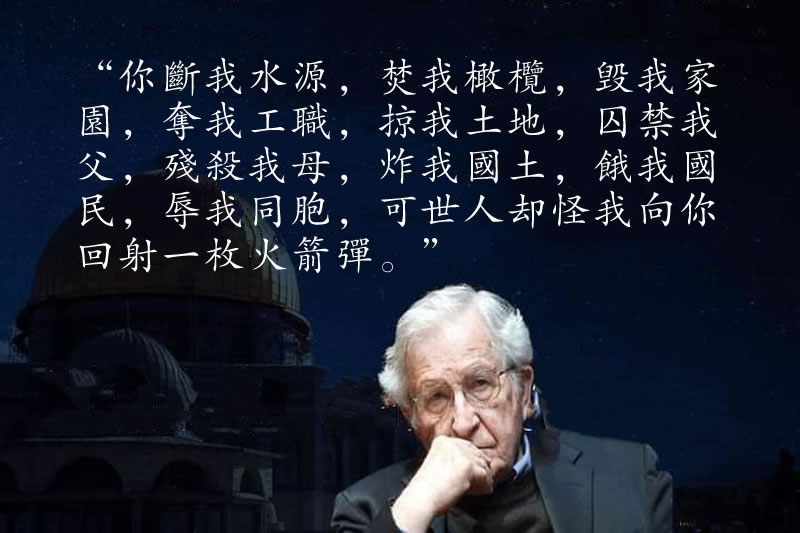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