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友人說,《聖學復蘇精義》被陳列於許多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的圖書館以及專家學者的書齋中,作為伊斯蘭文化的重要資料而被廣泛運用。可見,作為自我表述的權威典籍,這部名著正在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應該說,作為闡釋伊斯蘭文明的這樣一部著作,針對的不僅僅是穆斯林。穆斯林固然可從本著作中找回自我,但非穆斯林的朋友們也可從本著中就近讀解伊斯蘭,如果不是嘆服,至少不致有太多理解上的誤區。
同時,對於一些僅僅依賴西方學術資料的宗教問題專家、學者來說,這部著作為正面瞭解伊斯蘭提供了一個視窗。或許正是具有了這一含義,它才被我國權威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於是,這部百年以來僅作為我國寺內“大學”教材而不為平民所知的古典名著,始有了它的中文讀者。它用通俗而生動的語言向國人詮釋原汁原味的伊斯蘭文化。
《聖學復蘇精義》的發行與普及,其實是自我表述的復蘇。它獲得國內廣大學者和讀者的青睞,乃是對自我表述的首肯與定位。
我時常在想,無論在學術理論上,還是政治上、文學上,一些所謂的“國際準則”並非是無懈可擊的,而是大有商榷的餘地。
以諾貝爾獎這個被認為是世界上獨佔鰲頭的獎項為例,且不論自然科學(這方面而歐美國家領先尚可理解),單就文學獎而言,得主中歐美國家無疑占絕對優勢。但這並不能證明東方國家在文學上也始終處於弱勢。
有資料說,老舍再活一年就可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一些國人似乎迫不急待地為此而感到自豪。我覺得這與其說是自豪,不如說是在默認“歐洲中心論”,是魯迅所鞭撻的阿Q國民性的自然流露。
1988年,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獲諾貝爾文學獎,在中東,某些欣喜若狂的現象僅僅出自已經習慣於被表述的官方媒體,而廣大的知識份子、人民群眾內心更多的卻是尷尬、苦澀與悲哀。因為把納吉布·馬哈福茲推上這一“殊榮”的唯一因素是他的小說《街魂》張揚西方文明,而對伊斯蘭文明頗有微詞。
無獨有偶,2000年,瑞典文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法籍華人作家高行健。對此,中國作協負責人指出,“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這表明諾貝爾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2000年10月14日《光明日報》)
時隔不久,一貫敵視阿拉伯穆斯林的猶太人、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獲得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至此,把諾貝爾獎的政治意味和單邊主義暴露得無以復加。
無怪乎我國一位學者以《這顆葡萄是酸的!》為題,撰文抨擊諾貝爾文學獎,對它的所謂權威性提出挑戰。
失去了自我表述,加之其他種種人為背景和因素,我們的頭腦、生活中充斥著西方的定義、西方的術語乃至西方的人物和歷史。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西方學者(如蘇格拉底、培根等)在我國幾近家喻戶曉,而思想性和藝術性或許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伊斯蘭學者(如安薩里、伊本·泰米葉等)卻鮮為人知。
這種單一的價值取向不僅限制了我們的思想視野,妨礙著各種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對話,而且造成一種國際性的輿論誤導,把本意為“和平”、直接驅動了近代歐洲繁榮的伊斯蘭文化總是與“恐怖”、“威脅”等人造概念緊緊捆綁在一起。
正如美國學者埃斯波西托所指出的,“政治和傳媒把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同於激進主義、恐怖主義和反西方主義,嚴重地妨礙了我們的理解,制約了我們的回應。”“由於愚昧和原型思維相結合,歷史經驗和宗教文化沙文主義相結合,我們在對待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時,即使是抱著最佳的動機,也經常是盲目的。”(〔美〕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第250—251頁)
埃斯波西托早在1995年左右發表的這些見解,是對9·11後美國主演的所謂“反恐戰爭”的入木三分的詮釋。
只有深刻地瞭解“被表述”的現實及其社會影響,自我表述才會更加主動和充分,才會更加成熟和自信。
針對西方學術界炮製的所謂“東方學”,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在其名著《東方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對東方學而言,伊斯蘭存在著某種意義,這一意義最簡潔的表達可以在赫南的第一部著作中找到:為了得到最好的理解,伊斯蘭必須被還原為‘帳篷和部落’。殖民主義的影響,世界形勢的影響,歷史發展的影響:所有這些之於東方學家正如蒼蠅之於頑劣的男孩,被毫不留情地拍死,或只顧自己的玩耍而懶得去管——以免使東方單純的本質複雜化。”
“如果伊斯蘭的缺陷與生俱來,無法除去,那麼,東方學家會發現自己不得不反對變革伊斯蘭的任何嘗試,因為根據這一看法,變革即是對伊斯蘭的背叛:這正是吉勃的觀點。除了重複《李爾王》(KING LEAR)中傻瓜所說的‘他們會因為說真話而對我加以鞭笞,就像會因為說假話而對我加以鞭笞一樣;有時我甚至因為緘默不語而受到鞭笞’之外,東方人如何才能掙脫這些枷鎖而進入現代世界?”(《東方學》,三聯書店,第138—139頁)
這些血淋淋的“被表述”的文字,無情地告訴我們:自我表述已成為一種必然,責無旁貸。
應當指出的是,並非所有的“被表述”都帶有文化霸權的傾向,美國學者埃斯波西托的觀點就與西方學術界對伊斯蘭的一片謾駡聲形成鮮明的對照:
“當穆斯林擴散其統治和信仰時,他們證明,既是偉大的學習者,又是偉大的創造者……擁有巨大圖書館的重要城市知識中心出現在科爾多瓦、巴勒莫、尼沙普爾、開羅、巴格達、大馬士革和布哈拉,深陷於黑暗時代的歐洲在他們面前暗然失色……在這一進程中,穆斯林自由地借用其他的文化,展示了一種來自主人(而非僕人)和作為殖民者(而不是被殖民者)的開放精神和自信心。與20世紀不同,那時的穆斯林享有一種控制和安全感。”(《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第40—41頁)
“從宗教的觀點看,伊斯蘭教證明是一種更加寬容的宗教,它給猶太人和當地的基督徒提供了更大的宗教自由。”(同上,第47頁)
“這種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政策與當時基督教國家的狂熱偏狹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穆罕默德二世時代,巴爾幹的農民常常說,‘土爾其人的頭巾遠勝過教皇的三重冕。’”(同上,第54頁)。
這種客觀而具膽識的外來表述,為我們的自我表述提供了一種有效土壤,一種有力的佐證與支持。
這說明西方學者中仍不乏閃爍人性光芒的智者,他們中雖然有人依然恪守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但卻能擺脫西方式的傲慢,客觀而公正地看待伊斯蘭和穆斯林,一如看待其他宗教和東西方各民族。
因此,當代伊斯蘭學者有一種普遍的認同:伊斯蘭世界與西方,應通過平等對話解決衝突和危機,而不是簡單的訴諸武力。於是,“文明對話”一詞在伊斯蘭學術界不脛而走。
9·11後,美國把所謂“反恐”擴大化,不僅向伊斯蘭世界領土發動武裝侵略,而且矛頭直指穆斯林的意識形態,聲稱“宗教教育孕育了恐怖主義”,借此向所有穆斯林國家施壓。同時赤裸裸地袒護以色列的屠夫行經,而把正當的反侵略組織(如哈馬斯等)列入“恐怖組織”名單。
儘管這種不負責任的強權邏輯愈演愈烈,但伊斯蘭世界的主流派學者仍呼籲與西方(包括美國)進行多層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對話,通過對話(而不是對抗)消除誤會和偏見,增進瞭解和認同。
伊斯蘭學者們指出,決策者們應該十分清楚:西方是東方的一種文化需要,東方是西方的一種文化需要。東方與西方是一種競爭、互補的關係,而不是仇恨、對立的關係。
當代許多伊斯蘭學者認為,與西方進行對話,既是一種宗教義務,也是一種生活需要。好讓西方明白,穆斯林是一種使命的肩負者,而不是名利的追逐者;是仁愛的使者,而不是復仇的預告者;是和平的宣導者,而不是戰爭的鼓動者;是真理、正義的支持者,而不是謬誤、不義的幫兇。
穆斯林的使命是牽著困惑中的人類之手,把他們引向創造他們的主;把地球和穹蒼聯繫起來,把今世和後世聯繫起來,把人類和自己的人類兄弟聯繫起來;自己所愛,施予他人;己所不欲,不施予人;讓人類走出妒嫉、仇視的怪圈,走向彼此尊重、和平共處。
學者們認為,與十幾億穆斯林作對並不符合西方的利益;贏得穆斯林的友誼、尊重和信賴,才是西方的利益所在。我們應通過文明之間的對話,讓西方承認我們以伊斯蘭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而生活的權利,而這種權利並不以侵害西方、仇視西方為前提。
無論是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學術界,自我表述、文明對話,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伊斯蘭告訴我們,人性有向善的本能,有閃光的原質。這為自我表述與文明對話提供了無限的契機。
一位思想家指出,人性如閃光的金子,各種文化和習俗的積澱會給它蒙上塵埃,使它黯然失色。而我們的使命是擦去這些塵埃,讓人性發出原有的光澤和魅力。
雖然,世界政治和文化形勢錯綜複雜、風雲多變,但既然被表述的冬日已經過去,自我表述的春天還會遠嗎?
---------
文章來源:瀚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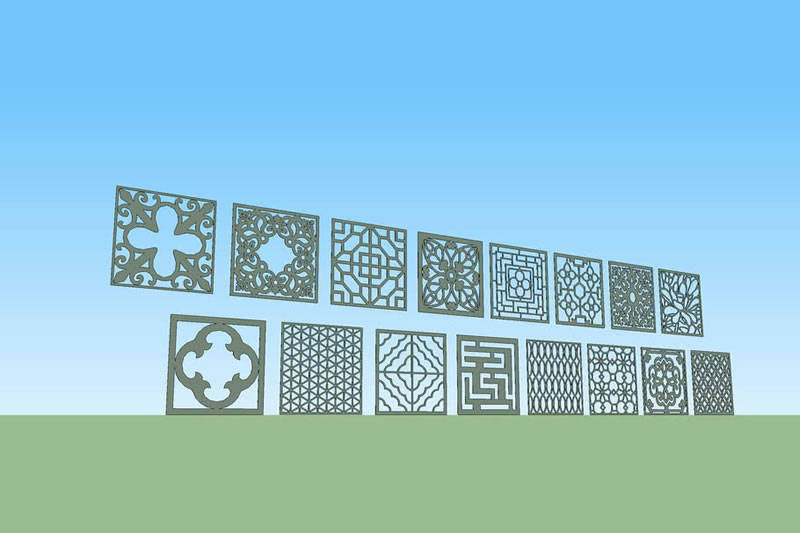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