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上的失落與衝突,是現代世界所面臨的共通現象。通常而言,認同危機的產生是由於全球化的趨勢所導致,因為全球化造成原有國界及舊有結構的消弭,而全球化導致的跨國遷徙更重塑了原有的社會及政治結構,因此對原有的根源及認同自然也會產生衝擊及影響。多元文化的存在,會讓一個國家主體民族發生認同危機,進而衍生出所謂的政治正確性標準,最終導致國內種族關係的緊張和族群間的衝突。
2019年3月15日,一名推崇“白人至上”白人種族主義的恐怖分子闖入新西蘭基督城兩座清真寺開槍,造成51人死亡,另有數十人受傷。本月13日,基督城舉行紀念活動,緬懷兩年前恐襲案遇難者,呼籲拒絕仇恨和分裂。然而,支撐此類“白人至上”種族主義思想的政治與媒體背景,依舊不容忽視。
近日,瑞士政府以極其狹隘的姿態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佩戴面紗。瑞士人民黨宣揚該法案的口號極其簡單粗暴:停止極端主義、停止伊斯蘭極端思想。 換言之,穆斯林群體的風俗習慣,已經被歐洲社會視為極端主義的代名詞。
該法案通過前,瑞士公民投票委員會主席、瑞士人民黨議員沃爾特•沃曼(Walter Wobmann)曾說:“我們瑞士的傳統就是時刻露出你的面龐,這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戴面紗則意味著極端主義思想,它是政治伊斯蘭的化身——政治伊斯蘭的潮流已經席捲整個歐洲,我們瑞士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沃曼先生的邏輯很簡單,他和種族分子一樣,堅信歐洲正在遭受伊斯蘭及穆斯林的暗中攻擊。
沃曼先生這一言論雖然極具種族主義色彩,但是,這種言論卻遺憾的成為當今歐洲乃至西方政壇的主流。此前,法國高等教育部部長弗雷德里克•維達爾(Frédérique Vidal)就曾妄言:“我認為,伊斯蘭極端主義正在蠶食我們的社會,高等學府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無法避免伊斯蘭極端思想的侵襲。”維達爾的此番言論,並不像一個發達國家高等教育部長能夠說出的話,它更像一個極端種族主義分子的撒潑言論。這種言論與思潮的本質,正是源自歐洲將伊斯蘭文明視為最大的假想敵,也反應了歐洲社會愈演愈烈的文化戰爭與衝突。
與此同時,維達爾部長的言論也從側面反映出法國乃至歐洲極左政府的最新戰略方針,其假想的“作戰物件”,正是穆斯林群體。我們清晰地看到,極左政客與種族主義分子達成結盟,他們異口同聲地將穆斯林稱為全民公敵,大肆宣揚伊斯蘭恐懼症,給穆斯林群體扣上“極端”“暴力”“恐怖”等帽子。
維達爾部長這番充斥著種族主義的言論,只不過是歐洲乃至西方社會伊斯蘭恐懼症大潮的冰山一角。僅就法國而言,各大政黨幾乎團結一致向國內穆斯林群體發起猛烈攻勢,不論是法國總統馬克龍還是他的強勁對手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二者雖然政見不同,但是,對於穆斯林,他們似乎都達成了默識,以不同的方式與方針發起抨擊與打壓,殊不知,二者的這種行為,只不過是為了吸引更多選票,激起民眾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政客們急需一個假想敵來轉移國內其他矛盾,將社會矛盾的焦點轉移至穆斯林群體之上。
而這一切,似乎都是歷史的重演。曾幾何時,猶太人被整個歐洲視為眾矢之的,被視為外來人種,而今,所謂的“外人”又成了穆斯林。以色列政治科學家阿米卡姆•納克曼尼(Amikam Nachmani)就曾直言:“猶太人曾經被歐洲視為另類人種,現如今,另類人則成了穆斯林。猶太人曾經遭受的歧視與偏見,如今已經轉移至穆斯林的身上。” 納克曼尼的這一比喻極為殘酷,但也是誰也無法忽視的現實,波士尼亞穆斯林的悲慘遭遇,就是血淋淋的實例。
我們必須承認,歐洲大陸乃至全球範圍內的文化衝突與戰爭早已醞釀已久,而穆斯林群體則是這場衝突與戰爭的附帶犧牲品。穆斯林並非我們最大的仇敵,伊斯蘭也並非我們所面臨的最大威脅,穆斯林在歐洲的存在與發展其實並非重點,它只不過是一場巨大文化、政治與利益衝突的陪襯。法國總統馬克龍其實也並沒有過多擔心或畏懼穆斯林,他的最大擔憂,是勒龐。而法國以及歐洲的文化大戰,也並不僅僅針對穆斯林,而是歐洲人、西方人對自身利益的擔憂與考慮。這種憂慮心理必然會催生出更深層次的危機感,很多衝突與問題依舊屬於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所遺留的惡果,“保衛世俗主義”,只不過是轉移社會矛盾與民眾視線的幌子而已,穆斯林群體不論如何努力,都無法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只能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屈辱求生存。
然而,法國並非個例。縱觀整個歐洲乃至西方世界,不論是政界還是主流媒體,都在各懷鬼胎地大肆渲染伊斯蘭恐懼症。此前,一直都是極左勢力宣揚反穆斯林言論,而今,右翼政黨也開始捲入這場鬧劇之中,新西蘭基督城清真寺襲擊案兇手,就曾高調宣稱自己是“驕傲的白人至上主義者”,而特朗普則被他視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就連遙遠的東方,也開始爆發針對穆斯林的襲擊事件。不久前,一名極右分子企圖襲擊新加坡一座清真寺,索性警方提前告破此案。嫌疑人坦言,他是受到新西蘭基督城清真寺襲擊案兇手的鼓舞,意圖在新加坡也掀起一場“巨浪”。這表明,針對穆斯林群體的偏見、歧視與打壓,並非偶然事件,而是當今世界的主流。
其實,白人至上分子、種族主義分子與所謂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之間有著諸多共通點,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暗藏著不可告人的政治與經濟目標,然而,這三者之間的區別卻極其令人費解,其中最主要的兩大不同點,在於以下兩個方面:1. 相比白人至上主義、極端種族主義思想,世人更為關注伊斯蘭極端主義,人們飽受白人至上以及種族主義思想的毒害,但是我們似乎依舊不願承認,白人至上主義者以及極端種族主義者才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敵人;2. 一直以來,所有打著伊斯蘭旗號行兇作惡的極端分子、暴力分子或恐怖分子都是媒體、政界與民間口誅筆伐的對象,然而,白人至上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思潮,卻在潛移默化中被忽視、被洗白。
包括法國總統、高等教育部長等人在內的所有政客之所以會不斷發表反穆斯林、反伊斯蘭言論,不外乎是為了謀求政治利益,但我們無權稱他們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在宣揚所謂的“歐洲阿拉伯”(Eurarabia)陰謀論。該理論認為,穆斯林正在全力佔領、奪取歐洲大陸。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應當時刻密切關注歐洲極右勢力的一舉一動,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給歐洲乃至整個西方帶來潛在的巨大威脅,而他們的所有顧慮與擔憂,都源自歐洲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感。
-----------
編輯:葉哈雅
出處:The Globe and Mail
原文:Europe’s identity crisis: Muslims are collateral damage in the continent’s culture wars
連結: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opinion/article-europes-identity-crisis-muslims-are-collateral-damage-in-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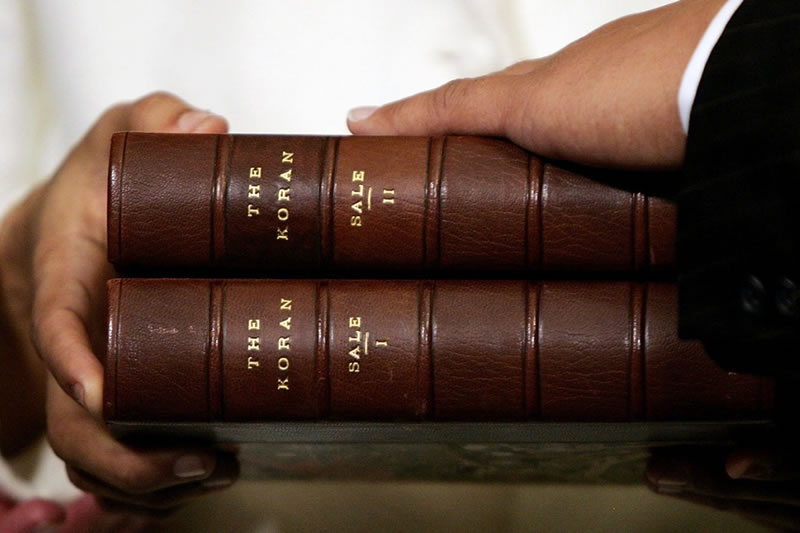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