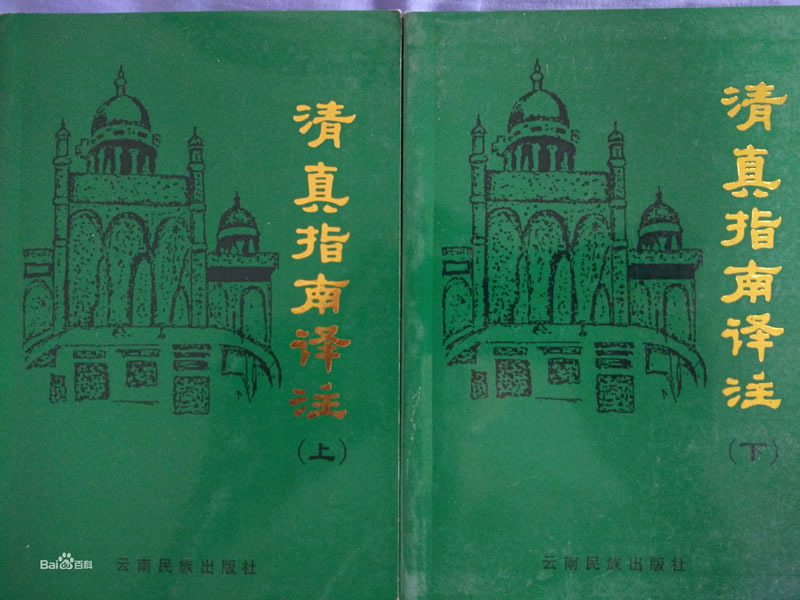
漢文伊斯蘭教著述是個很大的論題。國內的阿訇、經師、學者,從事伊斯蘭教著述的,不僅有漢文的,還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維吾爾文的作品,這裡僅涉及漢文方面的伊斯蘭教著述,下面簡稱為漢文著述。
一、漢文著述興起的社會歷史條件
伊斯蘭教於7世紀初創立後,有個自我發展、自我完善到宗教體制定型的過程。伊斯蘭教發展過程中,蘇菲主義具有宣教佈道的特點。其後來華的蘇菲傳教士把蘇菲神秘主義引入中國。它在中國吸引了一部分信眾、阿訇、經師和學者的關注,使得它的影響在漢文著述中有所反映。
伊斯蘭教於7世紀中葉傳入中國。由於伊斯蘭教是在不同時期,從不同地方分散地輸入中國,這就決定了它從傳入到大致定型,也有個發展、完善的過程;也是國人對伊斯蘭教瞭解由不多到有所瞭解的過程。
就漢文表述伊斯蘭教的行文而言,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書籍形式的作品。這包括正史、典籍、類書、方志等。在《舊唐書》中,已記載大食國派使節來華,其中談到其國已有34年,經歷三任君王。
杜佑的《通典》有杜環的“經行記”。宋代有關伊斯蘭教的記載逐漸多了起來。
早年的作者,可能主要是非穆斯林,他們對伊斯蘭教瞭解甚少,寫作的語詞大多以佛教的來比附伊斯蘭教。
第二類漢文記載,則是清真寺院內的對聯、中堂、碑銘。元代福建泉州“重立清淨寺碑記”有:“其教以萬物本乎天,天一理無可象(像——引者注),故事天至虔,而無像設。每歲齋戒一月,更衣沐浴……日西向拜天,淨心誦經。經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計一百三十四部,分六千六百四十六卷,旨義淵微,以至公無私、正心修善為表,以祝聖化民同急解厄為事。”
但有的文銘仍不能完全正確地反映伊斯蘭教的有關禮儀,說法有誤。有的碑文以佛教的達磨譬喻伊斯蘭教的信仰。有的碑文不乏迷信色彩。有的碑文以“天”稱謂真主,或以“事天”“拜天”表述其信仰。
就碑文作者而言,可能更多的是不瞭解伊斯蘭教的非穆斯林,從而表述伊斯蘭的行文有所欠缺、失誤。
由於一些文字作品或是碑銘對伊斯蘭教認識欠缺而有誤解,使得穆斯林知識界意識到有必要撰文為之補正,從而促使漢文著述的興起和發展。
大致到明末時,伊斯蘭教界的知識階層已經成長起來。就這一階層而言,主要是兩類人,一是有家學基礎的知識份子,他們自幼受到宗教教育,其中一些人成為阿訇、經師;二是受到儒學教育,之後又接受經堂教育的知識份子。這兩類人學成後大多數任阿訇、經師,有的成為學者。
就教內的知識階層而言,他們對伊斯蘭教的瞭解已極其清晰。明嘉靖七年(1528)山東濟南清真南大寺陳思撰寫的《來複銘》,已言及伊斯蘭教信仰。咸陽的胡登洲(1522—1597年)倡建經堂教育,推動了漢文著述的興起。經堂教育有13到14種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讀本,其中,蘇菲主義著作佔有1/3,這對其後漢文著述的內容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例如明朝進士、曾在戶部任職的詹應鵬(約1572—約1653年),在《群書匯輯釋疑》(失傳)的“跋”中:“志雲:‘其教專以事天為本而無像。’無像誠是也,第以為‘天’則非也。蓋所事者,宰乎天地萬物之主;惟主,故無像也。若曰‘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曰事主,非事天也。作此志者,或以萬物莫尊於天,故以天之名稱主,非其天即主也。閱者於‘事天’‘拜天’等語,俱當以‘天’字之‘主’字觀,慎勿作‘天’字觀也。”詹的說法強調的是“以天之名稱主,非其天即主也”,這無疑對上述有關“事天”“拜天”之說的一個極其明確地更正。
一般地說,事物的變化,外部僅是條件,內部才是變化的根據。明末清初,教內在主觀上也具備了漢文著述興起的條件,以適應伊斯蘭教發展的內在需要。
二、漢文伊斯蘭教著述的發展
應該說,漢文著述興起的先決條件是,應有正確掌握伊斯蘭教學理,同時又有漢文書寫基礎的阿訇、經師、學者來從事這一工作,以正確表述伊斯蘭信仰。
據趙燦的《經學系傳譜》,真回破衲癡為該書所寫序文說:“吾教自唐迄明,雖有經籍傳入茲土,而其理藝難明,旨義難傳,故世代無一二精通教理之掌牧,以至多人淪落迷途,漫漫長夜惹人甘醉夢之不覺也”。他接著談到胡登洲“慕本教經書,欲譯國語,以為斯土萬世法。”這是說,胡登洲已經意識到,從事漢文譯著的必要,他甚至“欲譯國語”,可惜未能完成。他的願望卻由他的弟子陸續實現。
胡登洲的第三代弟子,湖北江夏(今武昌)的馬明龍(1597—1679年)曾將《米而撒德》譯成《推原正達》;據說他還著有《醒已省悟》(《認已省悟》);
江蘇姑蘇(今蘇州)的張中著有《歸真總義》《四篇要道》;與張中幾乎同時的馬君實,著有《衛真要略》。
在當時的經堂教育中,馬明龍、馬君實、李定寰、常志美四位經師有“東土學者之四鎮”的美稱。可能由於刊刻、印製、流傳的原因,他們的著述,不及當今有中國“回族四大著作家”盛名的王岱輿、馬注、劉智、馬複初著述的影響。
王岱輿有《清真大學》《正教真詮》《希真正答》。馬注最為重要的著述為《清真指南》,有的著述,如《經》《權》二集已失傳。劉智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天方至聖實錄》。他對這三本書說:“典禮者,明教之書也,性理者,明道之書也”,而“至聖錄,以明教道淵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證道之全體也。蓋三書者,三而一者也;覆階而登,升堂入室,其庶幾矣。”另外有《五功釋義》《真境昭微》《天方字母解義》《天方三字經》《五更月》等。與劉智的同時代人黑鳴鳳,他對《天方性理》“本經”五章有《性理本經注釋》(單行本);對該書五卷每節行文均亦注釋。馬複初是個多產經師。除著、譯有《四典要會》《道行究竟》《大化總歸》《祝天大贊》《性命宗旨》《會歸要語》外,還摘馬注的《清真指南》為《指南要言》、輯王岱輿的《正教真詮》為《真詮要錄》,另有劉智《天方性理》的《性理卷五注釋》等等。
他們都是號稱“學通四教”的人。其實,在他們之間還有著許多具有重要影響的漢文作者。
王岱輿的弟子伍遵契先後跟隨常志美、王岱輿學習。他同樣將《米而撒德》譯為漢文,成為當今流傳的《歸真要道》,他還譯有《修真蒙引》。
另一位重要作者,著名經師舍蘊善(常志美的弟子)有《昭元秘訣》(《勒默阿忒》)《推原正達》《歸真必要》(《默格索特》)《醒迷錄》;只是《推原正達》和《歸真必要》未見流傳。
清代學者舍蘊善的弟子趙燦有上述《經學系傳譜》,馬伯良有《教款捷要》,米萬濟有《教款微論》,餘浩洲(劉智弟子)有《真功發微》(劉智曾為該書撰序),金天柱有《清真釋疑》,唐晉徽、馬安禮、龔楚翹有《清真釋疑補輯》,藍煦有《天方正學》,楊保元有《綱常》等。
應該說,進入明清時期,漢文著述大量出現。就此前的漢文著述而言,可以說有這樣幾個特點:
其一,忌譯《古蘭經》。有一段碑銘反映了這一思想:“禪經譯而便於讀,故至今學士譯之;而淨教之經,未通漢譯,是以不甚盛行於世……吾以為玄奘之譯,未必盡無訛……禪經譯而經雜,淨經不譯而淨不雜……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吾於經,取其不譯而已矣。”除了馬複初譯有《古蘭經》五卷(以《寶命真經》名義刊刻)外,並沒有通譯本,只有中阿對照的“亥聽”。民國以來到當前大致有10多個版本。
其二,漢文著述的發展,形成漢學派。它不同于反對漢文翻譯、漢文書寫宗教問題的經學派。
其三,漢文著述發展緩慢,數量受限。但在這時大致解決了此前碑銘中出現的一些欠缺和誤解。
其四,漢文著述的發展,經歷了艱難的內在的爭辯。目前,人們可以讀到的《中國回族典藏全書》中有所體現。(它包括的面極其廣泛,並不全是宗教著述;就宗教著述而言,從中清代以來的著述,居於相當多的數量。)
三、漢文著述的基本內容
漢文著述的基本內容,涉及教法、禮儀、倫理方面的有《天方典禮》《五功釋義》《修真蒙引》《衛真要略》《真功發微》等著述,其中,有的還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三綱五常問題。其實,有關三綱五常修齊治平的內容,不僅在著述中得到反映,甚至在清真寺的碑銘中也可看到。
關於教義、教旨或信仰方面,漢文著述主要涉及的是性理學說。這在王岱輿、馬注、劉智、馬複初的著述中都有所反映。這是值得重視、值得推崇的伊斯蘭思想。
(一)關於語詞“真”
從宗教意義上說,“真”是真主、真宰的學理性替代詞;被視為造化宇宙萬有(含精神性實體和物質性實體)的本原;從哲學意義上說,它是中國伊斯蘭哲學最高的範疇。
作為精神性實體,“真”於先天(理世、上界)顯化;其顯化是一切物質性實體產生、發展、變化的根源。“真”顯化後,一切精神性實體或單獨存在,或寓於物質性實體之中,與物質性實體一同活躍於後天(象世、下界)。
“真”顯化出宇宙萬有,並不影響其超然存在,也不因其顯化而有所增減。
“真”含有“真一”“數一”“體一”三品;它們分別是“真”的體、用、為,即“真一”為“真”之體,“數一”為“真”之用,“體一”為“真”之為。“真”借助這三品完成自我顯化。
(二)關於語詞“真一”“數一”“體一”
由於“真一”作為“真”之體而被顯化而出,他既與“真”處於同一層次,又與“數一”“體一”處於低於“真”的層次。或者說,“真”(=“真一”)“真一”—“數一”—“體一”
“真一”處於隱顯不同狀態。他的隱顯變化,分為自顯與外化兩個不同階段。自顯是“真一”處於隱秘、靜穆時的內在變化,外化則是“真一”由隱秘、靜穆狀態而顯現、活動的外在變化;這一變化亦即由靜而動、由隱而顯、由內而外、由一而多的顯化,或者說,即“真一”顯化出宇宙萬有。
“真一”的顯化,是通過“真一”之體的“用”實現的。這樣,在“真一”自我之外,有了非我,即“數一”。
“數一”並非一二三四中居於數碼首位的一,也不是第一、第二、第三順序中的一。“數一”源自“真一”;在兩者關係上,“真一”為主,“數一”為僕。
“數一”同樣具有體、用、為三品。天地萬物的一切精神性實體和物質性實體均由“數一”而產生、形成。“數一”乃造化宇宙萬有的原型和摹本,它包容先天的性理和後天的一切形器。
中國傳統哲學的無極、太極、兩儀、四象,在“數一”的顯化活動中居於重要地位。即借助無極太極之說,構建了先天後天(理世象世、上界下界)的宇宙萬有得以產生、形成的根據。或者說,無極處於先天(理世、上界),太極處於由先天到後天(由理世而象世、由上界到下界)之間的過渡;亦即先有先天無形性理由一而多的衍化,後有後天有形、無形的氣相、形器的由一而多的化生。
在“數一”由先天向後天衍化過程中,因氣盛理微,無極——作為萬物之母的性原——過渡到太極,太極而後為兩儀,兩儀而後為四象,兩儀、四象則起著具體衍化為宇宙萬有的、由精神變物質的作用。這樣,宇宙萬有得以產生、形成。
在精神變物質過程中,隨之出現了造化天地萬物所必須的時空條件。其中,“數一”在先天起著造化宇宙萬有的代理作用,在後天起著引導穆斯林的作用;它是“真一”顯化宇宙萬有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
就後天有形的宇宙萬有來說,唯有人能承擔“數一”所賦予的使命。因此“數一”所衍化的“體一”,專門討論的是人,而不是其他衍化物。
“體一”表述的是人如何體認“真一”並複歸“真一”的問題。為複歸“真一”,首先必須體認“真一”,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認主”。因為在宇宙萬有中,唯有人具有認識能力、並能包容一切,但人需要有至聖的引導,通過“認己”而“認主”,這樣,才能複歸真主。
伊斯蘭教關於造化天地萬物“本以為人”之說,提出一個非常形象的說法:“我是隱藏之寶,我喜人認我。我造化人,只為認我。”這是說,為使寶藏顯現出它的俊美和價值,需要被認識;真主造人,就是為了讓人“認主”。這裡,有著目的論的痕跡。
中國伊斯蘭哲學在形成過程中,不同程度的受到蘇菲主義的影響。表面上,“體一”也具有體、用、為三品。它的體認是個體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實際上,它是蘇菲精神功修三乘道路(禮乘、道乘、真乘)的三個不同發展階段。“體一”到此並未完成他的存在的使命。他還必須實現其最終目的,即如何“認主”。
作為“數一”,即至聖在後天的使命而言,就是引導信眾複歸真主;就一般信眾而言,則是在至聖的引導下複歸真主。
這樣,也就完成了從“真一”開始經“數一”“體一”而又返回“真一”,從而形成一個封閉的思想體系的構建。
(三)關於“三一”
“真一”“數一”“體一”三者被稱之為“三一”。
王岱輿關於“三一”有如下的說法。他說:
蓋辨一有三:曰:‘單另之一’、曰:‘數本之一’、曰:‘體認之一’。單另之一,乃天地萬物之主也;數本之一,乃天地萬物之種也;體認之一,乃天地萬物之果也。(《清真大學》題綱)
所謂“單另之一”,即“真一”;“數本之一”即“數一”;“體認之一”即“體一”。表面上,“三一”說的是“真一”“數一”“體一”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或者說,它說的是主、種、果之間的關係問題。實際上,它是一個龐大的本體論、宇宙論(含宇宙起源論、宇宙演化論、人性論)、認識論的思想體系。
那麼,真一、數一、體一三者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可以說,應瞭解“真一”“數一”“體一”三者均源自“真”,他們都是“真”的自我顯現。“真一”“數一”“體一”三者“異名同實”,都是“真”的體—用—為的顯現,名義上為三,實際上則為一。“真一”“數一”“體一”三者不可分割、相互貫通。三者無先後之分,但有主僕之別,即“真一”為主,而“數一” “體一”為僕。
中國傳統哲學關於體—用關係,是一個重要的哲學範疇。如何理解上述的三品?一種表述形式,可以說是繼續沿襲了傳統的體—用模式,即體—體用—用;還有一種理解方式,即由體而用,由用而為,則是體—用—為。不管哪種形式,都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的體—用關係的發展。
我們應將漢文著述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往往一說到中國傳統文化,就認為指的是儒釋道。當我們研究漢文著述、特別是王岱輿等人的思想時,應該看到他們的著述雖然涉及的是源自境外的伊斯蘭思想,但他們通過引用、借鑒、加工、改造後,使伊斯蘭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達到有機的融合,已經開花結果,構成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哲學的有關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伊斯蘭哲學。
我們不能再把漢文著述、再把其中承載的思想,視為外來思想的複述。正如佛教本來是外來宗教、外來文化。隨著它在華夏大地上的傳播,終於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我們談到中國伊斯蘭思想、中國伊斯蘭文化時,同樣應該認為它們已經構成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思想寶庫中的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我們同樣應視如是觀。
漢文著述所闡釋的思想,仍然保留著伊斯蘭信仰的內涵。它的主旨在於維護伊斯蘭教信仰。這是中國傳統思想所沒有的。就是說,漢文著述既不是類似外部世界的、原封不動的、純粹的伊斯蘭思想的複述,也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單純的再現,而是具有中國與伊斯蘭雙重品格、雙重特色的思想和文化,或者說,與外部輸入的、原初的伊斯蘭思想已有所發展、變化。這就不僅僅是簡單的量的增添,而有其新的質的補充。這無疑是宗教中國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和重要成果。
伊斯蘭教是在幅員廣闊、民族眾多的中國流傳的。我所理解的“宗教中國化”的發展,也就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發展。只有這樣理解,才符合歷史發展的事實。才能寫好中國歷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宗教史。至於究竟有哪些新質,應予以細化的研究。
我們對漢文著述的研究,還沒有重視到應有的高度。這應該引起大家的參與、重視和關注。
(原載《中國穆斯林》雜誌2017年第五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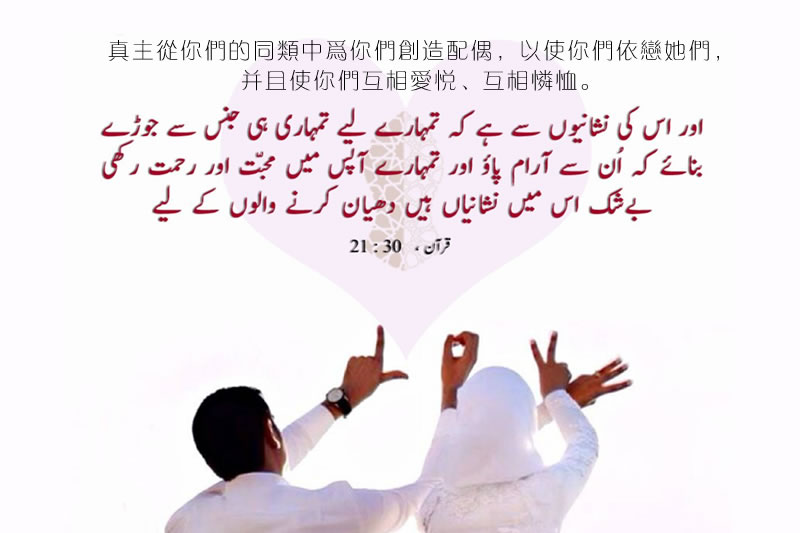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