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心觀察、研究穆斯林生活規律的人不難發現:科學在他們的生活中不是以一種理論的形式出現,而是一種流動的生活;科學在穆斯林那裡不是僅僅為一些科學家和文人們所張揚的一種理論,而是雖目不識丁的文盲、普通老百姓也自覺遵守的一種“生活習俗”。
一種“科學”,怎樣在穆斯林現實生活中根深蒂固、雷打不動而成為一種“習俗”的呢?美國學者伯爾曼在其著《法律與宗教》中指出,一種生活秩序,“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在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科學被納入信仰範疇,成為“社區主命”(如醫學、化學、物理、天文等學科),或“聖行”(如講究衛生、勤於刷牙等);同時,這種科學首先立足于信仰,向信仰負責;至於它對人的“利益”則是一種“結果”,而不是“目的”。
一
信“前定”是穆斯林信仰六要素之一。它對穆斯林生活的“科學效應”是顯而易見的。穆斯林認為萬事成敗的決定性因素是真主,而不是人,也不是某個物質因素;同時,人奉命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積極進取,鍥而不捨,做到力所能及的一切。在伊斯蘭看來,“物質決定論”是以物配主的行為(什勒克);同時,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則屬否認真主的行為(庫夫爾)。因此,在“採取行動”與“托靠真主”之間、“謀事在人”與“成事在主”之間實現一種心理平衡。這樣,在成功時,不會沾沾自喜、自命不凡,而是將成功歸於主的援助;在失敗時,也不怨天憂人、哭天搶地,而是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同時,把它歸於真主的總體安排:“或許你們討厭一件事,而這事對你們有好處;或你們喜歡一件事,而那事對你們有壞處。”(2:216)
“真主決定論”使穆斯林不至於把挫折失敗乃至生命財產的損失簡單地歸結於某個人或某件事,從而超越擺脫了許多毫無作用卻有害身體的煩惱與懊悔,心理上獲得一種超脫與解放。這種務實的態度,使穆斯林不會輕易屈從于人為因素、物質因素的壓力(如考不上大學時不會抱怨自己沒有一個“好爸爸”、評不上職稱時不會抱怨某個領導……),而是接受已知的一切,在未知領域積極進取。每個人一生都在追求幸福(不管是婚姻、事業的),而幸福又往往與我們失之交臂,當我們對生活中許多的事感到力不從心、鄒紋又悄悄爬上我們眼角的時候,我們仿佛才會明白生活本身就是一曲幸福與痛苦、安逸與患難、歡笑與血淚的交響樂。對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始終保持一種平衡心理,既是信仰的要求,又是保護身心健康的最佳途徑;這種務實、豁達的心態,得到美國學者卡耐基的科學詮釋:“你是不是幸福,取決於你自己的思想。”然而,這一平衡心理素質的起因並非是“科學”,而是“信仰”。正是有了信仰的動力,才使這一平衡心理不是心理學家和科學家的“專科”,而是普通穆斯林的思想意識和心理素質。甚至他們對“死亡”的態度也是那樣坦然與樂觀:“我們都是屬於真主的,我們最終將統統回到他那裡去。”(2:155)
二
禮拜是“主命”,拜前小淨是禮拜的條件之一;每週五洗一次大淨(沐浴)是“聖行”,而身無大淨(如夢遺、性交等)後大淨又成為“主命”;刷牙是可嘉聖行,穆聖對此特別強調:“假如教民不嫌麻煩,我一定讓他們每番拜刷一次牙。”禮拜要求“三淨”:身體淨(前述大小淨)、衣服淨、拜處淨:性交後必須大淨的律例使大淨(沐浴)成為生活不可缺少的環節,同時對性生活堪稱一種節制;遺精、夢遺等壞大淨的律例對種種非禮意念和活動堪稱一種制約,從而有益思想純潔和身心健康……這一切默默地構成一套有規律、有秩序的科學生活方式。然而意味深長的是,它們是在“完成宗教義務”的神聖意識中自然進行,成為信仰在生活中的自然延伸,卻不是出於“提倡科學”的動機。當現代人把每天刷牙、睡前洗腳作為“科學生活”而奉行唯謹的時候,它們只是千百年來穆斯林實際生活中的一個細節,穆斯林不動聲色地在恪守它但絕不以“科學”、“衛生”相標榜;他們覺得那很正常,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除此沒有別的生活形式。一個旅途中的穆斯林,儘管疲憊不堪,而且舉目無親,但他不會忘記去找清真寺,然後小心翼翼地洗一個小淨或大淨,然後站到自己的主面前至少禮兩拜……從衛生、科學角度去看,這些舉動無疑對身心舒適、心理安然有莫大的作用。在穆斯林看來,這首先是信仰的流露、心靈的渴求,是拜主為己任的穆斯林生活的一部分。一個遠處窮山僻壤、鬥大字不識一升的農民或牧民,儘管不懂刷牙的“衛生道理”和“科學道理”,甚至根本沒聽說過“科學”“衛生”這些詞彙,但他的信仰促使他去刷牙、去沐浴,從而去過一種實際上是科學的生活。科學與生活融為一種天然的默契,與一廂情願式的“科學理論”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三
早起、節制飲食等被視為現代科學生活的內容,而根據伊斯蘭的要求,晨禮這一主命拜使穆斯林自然地把早起作為履行主命的首要程式,甚至早起成為穆斯林區別于非穆斯林的一個鮮明持征。關於節制飲食,穆聖說:“胃的三分之一留給吃,三分之一留給喝,另三分之一留給呼吸。”又說:“我們是這樣一個共同體:不饑就不食;食而不求過飽。”每年一月的齋戒,堪為節制飲食的週期性訓練。但穆斯林早起、節制飲食,首先是為了遵守聖行,取主喜悅,至於“衛生”作用,則是這些聖行的必然結果。
根據美國成人教育專家卡耐基的研究,克服失眠的最好辦法是祈禱,而睡前祈禱對穆斯林來說是“聖行”,是穆聖生前長期堅持的生活習慣。試看聖訓禱詞:“主啊!我以你的名義入睡,以你的名義起床。如果你拿去我的生命,求你饒恕它;如果你放赦我的生命,求你保護它,猶如保護你清廉的僕人一樣。”這是何等安寧、怡靜、豁達的意境,有全宇宙的創造者保護,還有什麼煩惱能使人“失眠”呢?而穆斯林這種起居習慣與世俗哲學不同:由於睡前祈禱是“遜奈”(聖行),是近主的行為,使這一本來對人自己有好處的“習慣”具有了一種神聖性;鑒於它的內容樸實無華,切中人類心理最深層的“隱患”,而不屬深奧難懂的哲學,故適合各個階層的人,因而具有了一種“普遍性”。“神聖性”與“普遍性”使得這一生活規律首先是一種“功修”,其次才是一種“科學”,這為它植根于穆斯林的生活提供了不可動搖的信仰基礎。
類似的聖訓還有:睡覺時側右睡,因為人的心臟在左邊,側右睡覺避免了對心臟的壓力,從而便於呼吸,同時使胃裡的食物及時進入十二指腸,利於消化;開齋時首先用棗,因為封齋的人需要及時補糖;參加游泳、騎馬、射箭、跑步(穆聖曾和聖妻賽跑),以增強體質……這些包含豐富“科學”內容的活動,以“聖行”、“功修”的內涵融入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它帶給穆斯林的,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科學”、“衛生”利益,更主要的是賦予他們一種信仰之美、昇華之美。
四
一般人都知道伊斯蘭禁食豬肉、禁止喝酒,它們的科學意義不僅為穆斯林所熟悉,而且即便是非穆斯林中也幾乎成為不爭的事實;同時,根據伊斯蘭的立法原則,凡是有害身體的都屬非法。但是,穆斯林生活哲學的獨特之處在於:當他們以自己的覺悟選用食物時,首先想到:這是主的命令,執行了它就會博得主的喜悅,就會得到主的恩賜;至於這一行為對自身的利弊則不是他們所追求的首要目標。這樣,一種實際上是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由於有了不同凡響的意念,而成為一種流動的信仰,一種“習俗”成了“對主的敬拜”。這一認識至關重要:它避免了從純科學角度去解釋某些伊斯蘭律例造成的牽強和被動。馬汝鄰先生曾有一篇文章批評王靜齋、馬堅等前輩對禁食豬肉所作的“科學解釋”,說豬肉中有絛蟲,而對它作過高溫消毒處理的話,穆斯林仍然未必會吃!雖然馬汝鄰那篇文章企圖否定禁食豬肉的“科學道理”,但平心而論,他從反面向我們提出了純科學角度解釋教律的弊端。是的,正因為這些禁律源自信仰、源自對主的絕對服從,而不是源自“科學道理”,穆斯林才對它恪守不違(即便豬肉對人體無害也罷!)。
在現代一些城市的公園裡、大街上,常常會看到一些老人清晨鍛煉身體的情景,他們為了“延年益壽”而不遺餘力、一絲不苟,其執著精神令人感動。然而,如果我們去探討穆斯林某些禁律的科學內涵、五番拜對身體的陶冶與鍛煉、封齋對身體的保護作用等等,就會發現兩者有著天壤之別:非穆斯林的動機僅限於“個人利益”,即健康長壽;而穆斯林的動機首先是取主喜悅,其次才是“個人利益”。即便是追求“個人利益”這個層面內,兩者也截然有別:非穆斯林看來,健康長壽是增強體質的終極目標;而穆斯林看來,身體乃至生命屬於真主,人無權侵犯自己的身體,因此,穆聖對長守夜功而影響了身體的阿慕爾說:“你對你的眼睛有義務,對你的身體有義務。”故保護身體首先是向自己的信仰負責的行為,是接近真主的一種“功修””;而身心健康,則是這一功修、這一流動信仰的天然附屬品。可見,作為非穆斯林最高追求的“貼身利益”,卻是穆斯林實現終極價值(取主喜悅)過程中附帶的小目標;確切地說,這一“利益”是一種油然而生的結果,卻不是首要目標。
這種不同價值取向的影響是巨大的:
(一)雖然在“保護身體”方面有著共同點,但穆斯林是“為主”,非穆斯林是“為已”,這使前一動機蘊含一種超越性和神聖性,因而容易堅持和恪守。如穆斯林的五番拜功、每年一月的齋戒、勤於沐浴的風尚等,已經生活化、社會化;而非穆斯林鍛煉身體、戒除煙酒等行為往往出於偶然的原因、一時的衝動,因而缺乏一貫性、持久性。
(二)由於穆斯林的動機是“為主”,這就把一種給自身帶來“利益”的行為和宇宙的主宰以及自己所追求的神聖事業聯繫起來,使“保護身體”這一似乎十分俗氣的行為有了一種超物質、超時空的永恆意義;而非穆斯林“延年益壽”為宗旨的保護身體的行為,充其量屬於“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而無法到達超越自我的境界。
五
在一些場合,如果有人對不在場的人蜚短流長,有覺悟的穆斯林會馬上站出來制止。這就是穆斯林生活中“禁止背談”的文化內涵。除了禁止“背談”,古蘭經、聖訓還禁止“發怒”、“猜疑”、“妒嫉”、“刺探他人隱私”等。這些人類常犯毛病不外乎一個原因,那就是心理的不平衡;而這些心理活動超出常規時,即產生心理扭曲、心理變態,從而危及身心健康。據有關資料顯示:妒嫉過分會使一些婦女患不育症;而聖訓中將妒嫉喻為“燒毀一切善功的烈火”。當有人要求穆聖給他一個綜合性囑咐時,穆聖說:“勿怒。”“發怒傷肝臟”是中國人由來已久的說法,是傳統中醫學十分重視的醫療內容。穆聖說:“站著動怒時應坐下;坐著動怒時應站起來。”改變身體的位置,有益於緩衝怒氣。美國學者卡耐基認為發怒時應該馬上去做一樣工作。穆聖對動怒者的良方是:“發怒時速去洗小淨。”其寓義是深刻的:
(一)現代醫學認為動怒時體內產生一種病毒,上廁所可及時排除這種病毒;穆聖命人動怒時洗小淨,必然要先解手後做小淨,附帶著應用了現代醫學所開處方。
(二)洗小淨是一個系列動作程式:洗手、漱口、嗆鼻、洗臉、洗臂、抹頭、洗腳……加之開頭和結尾相應的念詞,這系列井然有序的動作,對轉移動怒者的注意力無疑具有相當的作用。
(三)由於小淨是禮拜的條件之一,故屬於“拜主”的一個程式,而不同於一般世俗的洗漱動作。它是在一種神聖感中完成;精神感受與外在的洗漱活動互相交融,對動怒者是一種“雙重洗禮”,從而有效地排除不利健康的因素。
類似的聖訓比比皆是,幾乎涵蓋穆斯林生活的各個領域。探討它們的“科學性”並不是本文的主旨。我們只想說明的是,這些具有科學內涵的生活現象,以信仰、功修為起點而為穆斯林所遵循、格守;緊跟穆聖、取主喜悅的神聖目標使它們的“既得利益”和“物質效應”居於從屬地位,成為一種自然的流露,而非終極追求。這樣以來,穆斯林的生活中,“科學理論”尚未產生之前就有了“科學事實”,致使目不識丁的平民百姓也得以享受這些“科學成果”。這或許就是信仰和世俗科學的本質區別吧?
六
東西方的歷史學家,驚歎于中世紀穆斯林的科學文化,僅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燦若星漢,舉不勝舉——塔伯裡:歷史學家、古蘭注釋家、法學家;拉齊:哲學家、醫學家、音樂學家;安薩里:哲學家、倫理學家、心理學家;伊本魯西德:哲學家、醫學家、法學家……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那麼,這種“科學奇跡”是怎樣產生的呢?這要從穆斯林獨特的科學觀和文化觀中去尋找答案。
或許宣導知識和科學方面莫過於以下這段聖訓了:“求知是每個穆斯林的主命。”它蘊含了穆斯林對待知識的特有認知:“主命”在伊斯蘭法學中的定義是“不完成就會受到懲處(入火獄)”。那麼,求知是“主命”意味著:不學無術、甘願無知是罪過,要受火刑;求知是“主命”,則求知是真主喜悅的行為,是接近真主的一種途徑;求知是“主命”,那麼,穆斯林每學得一點知識,就向真主接近了一步;反之,倘若自暴自棄、甘願無知,則離真主愈來愈遠。“真主的僕民中只有知識份子才敬畏他。”(35:28)由於求知是主命,則必須把掌握的知識和科學用於主所喜悅的、給人類帶來福利的事業,而不是把它用於塗炭生命、滅絕人性(如二戰中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屠殺行徑、美國在日投下原子彈造成30萬人死亡,等等)。這種獨樹一幟的文化觀和科學觀,使穆斯林的科學文化不僅獨步中古,光芒萬丈,而且,它以信仰為中心,向各個學科領域幅射,從而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科學運動。
此外,中世紀穆斯林科學文化的繁榮,和伊斯蘭關於“代治”的認識論不無關係。根據伊斯蘭的觀點,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真主為人征服了天地間的一切。因此,伊斯蘭把發展科技、提高生產力、開發天地間的一切能源視為人類“代治”使命的行為,視為對真主的服從,真主因此而賜予他後世的報酬(儘管人類代治大地的過程其實也是為自身謀幸福的過程)。同時,根據伊斯蘭的觀點,不發掘大地的寶藏、不利用真主為人預備的宇宙能源、不進行科學探索,是違抗主命、怠忽職守的行為。這樣的人,既失去了今世,也無法得到後世。正是這種認識,使中世紀穆斯林的學術活動、科學探索不僅僅限於一些學者和科學家,而是成為一種普遍的風尚。不管是用科學論著等重量的黃金獎賞科學家的麥蒙等哈裡發,還是那些歐洲一片黑暗的時候在人類科學舞臺獨領風騷的穆斯林科學家,都把科研活動以及對它的大力提倡,看做是對真主的敬拜,是感謝真主巨集恩的一種表達方式。無怪乎穆斯林的“實驗科學”短期內傳到了歐洲,引起了歐洲各國的“文藝復興”,為歐洲後來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以上從六個方面探討了務實的、信仰化的科學在穆斯林生活中的體現。我想,由於信仰的作用,科學融入一個群體的生活,簡直與他們的意識和行為水乳交融、渾然一體。這種現象,是否值得我們的哲人們深思呢?
【來源:瀚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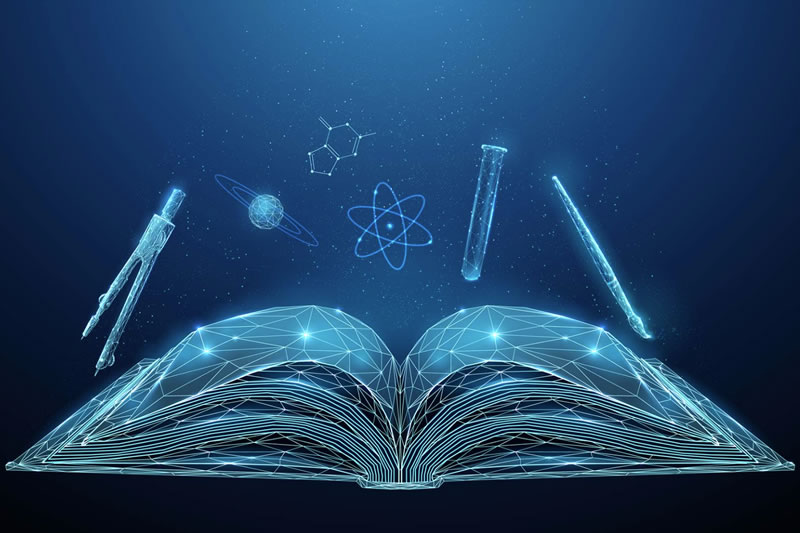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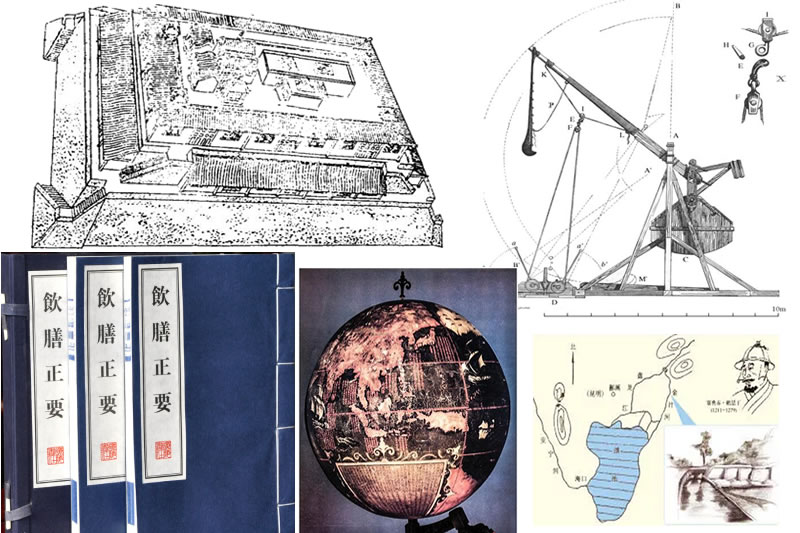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