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西元7世紀起至其後的一、二百年間,阿拉伯人初步建立起一個西起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脈,東至大唐西部邊境與印度信德地區的橫跨亞、非、歐的世界性帝國——阿拉伯帝國。這一帝國的文明達到很高的水準,其科學、技術及文化成就,即使在帝國之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仍然保持領先地位,直至文藝復興,世界科學中心才由那裡轉往歐洲。阿拉伯帝國的科學成就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不可磨滅的印記,它在人類文明史上佔有重要的篇章。
與其它文明不同的是,阿拉伯帝國的科學成就與伊斯蘭是密不可分的。因為在伊斯蘭進入阿拉伯土地之前的漫長歲月中,蒙昧的阿拉伯人以及帝國內其他一些後來皈依伊斯蘭的民族完全籠罩在古埃及、印度、希臘、羅馬與波斯文明的陰影之中。隨著阿拉伯人版圖與活動範圍的擴張,許多民族如波斯人成為信奉由阿拉伯人率先傳播的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由於踐行伊斯蘭所宣導的真主之下人人平等的思想,因此帝國的阿拉伯人及其他民族在科學文化上持寬容與兼收並蓄的態度,從而大大推動了那個時代科學的進步和發展。
二、科學成就
1、數學
任何十指健全的人都知道,從一數到十,最方便的記錄方法是使用阿拉伯數字。這種奇妙的數字是聰明的阿拉伯帝國的穆斯林從印度人那兒吸收,並將之介紹到西方與東方的;同時,這些穆斯林向世界推廣了數字“0”與十進位。具體地說,正是借助花拉子密(al’Khwarizmi,拉丁語名為Algorismus,西元780~850年)著名的《印度計算法》一書,這種對世界產生難以估量影響的奇妙數字才為世人瞭解並接受。因此,人們把這種數字稱作阿拉伯數字。今天,阿拉伯數字已經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了。
阿拉伯數字無疑是方便而先進的數位體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愛好數學的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Sylvester II,西元945~1003年,任職:西元999~1003年)大約在西元1000年前後,曾經試圖在基督教世界中推廣使用這種數位體系,結果卻收效甚微。
中學生進入中學學習的第一門數學課程是什麼?答案是代數學。代數學是人類步入數學以及其它自然科學領域的基礎。雖然代數學的萌芽久矣[代表人物:丟番圖(Diophantus,西元200?~284年?)],但是它是在阿拉伯帝國的穆斯林手裡正式成為數學的一門學科的。因此當後來的數學家們孜孜不倦地學習花拉子密的代數學著作時,沒有人懷疑代數學是阿拉伯帝國的穆斯林創立的。
這位偉大的數學家在其著作中首次明確提出,代數學的數學問題都是由根(x)、平方(x2)和數(常數)三者組成,並且分六章敘述六種類型的一、二次方程的求解問題。花拉子密最具影響的代數學著作——《算術和代數論著》,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關於代數學的論著,此書的拉丁文譯本直至文藝復興時期還作為教科書在歐洲的大學中被廣泛使用。
花拉子密對代數學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由他的名字——al’Khwarizmi的拉丁語譯名——Algorismus,不僅派生出“Algorithm”或“Algorism”(“運算法則”或“十進位”),後來還演變出現在的對數一詞——logarithm(簡寫為“log”);算術“arithmetic”一詞的來源也與之類似。他在代數學中使用“還原、移項”一詞的阿拉伯語音譯“al-jabr”,傳入歐洲後便演變為我們今天使用的“algebra”(代數)。
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史學家、《科學史導引》的作者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年)對花拉子密的評價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數學家、迄今所有時代最崇高者之一”。他在讚揚花拉子密的代數學的意義的時候說:“在數學上,從希臘人的靜態宇宙概念到伊斯蘭的動態宇宙觀,第一步是由現代代數學的奠基者——花拉子密邁出的。”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在《阿拉伯通史》中對花拉子密評價說:“他是伊斯蘭教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對於數學思想影響之大,是中世紀時代任何著作家所不能及的。花拉子密不僅編輯了最古的天文表,而且編寫了關於算術和代數學的最古老的書籍。”
阿布·卡米勒(Abu Kamil,西元850~930年)是花拉子密代數學的直接繼承者之一,著名的《代數》一書就出自他的手筆,他本人也表明,他在代數學方面的工作是建立在花拉子密代數學基礎之上的。阿布·卡米勒在代數學上的地位,可謂上承花拉子密,下啟卡拉吉(al-Karaji,西元953~1029?年),而且還為義大利數學家斐波那奇(Fibonacci,1170~1250年)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外他還寫了《測量與幾何》與《計算技巧珍本》等諸多數學著作。《代數》其實包括三個部分的章節,即①二次方程的解法,②代數學在正五邊形與十邊形上的應用,及③丟番圖等式與趣味數學問題;其中,第二部分章節,就是把埃及、巴比倫的實用數學與希臘的理論幾何相結合,用幾何學方法證明代數解法的合理性。《測量與幾何》是一部指導大地測繪的實用性書籍,例如講解如何測量各種不同圖形的對角線、周長、面積,以及測量各種不同形狀物體(六面體、棱柱體、棱錐體及圓錐體)的體積與表面積。《計算技巧珍本》則涵蓋幾何和代數兩方面的內容,但其主要成就是關於四次方程的個別解法與如何處理無理係數的二次方程。除了上述留傳下來的三部著作之外,西元10世紀的《科學書目》一書還列舉了阿布·卡米勒另外一些著作,包括Book of Fortune、Book of the Key to Fortune、Book of the Adequate、Book on Omens、Book of the Kernel、Book of the Two Errors和Book on Augmentation and Diminution。
奧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1048~1131年,兼詩人)是《代數問題的論證》(簡稱《代數學》)一書的作者,在數學尤其是代數學歷史上堪稱最傑出者之一。作者開創的用圓錐曲線解三次方程的方法,並依此將三次方程進行分類,可謂是對代數學發展的卓越貢獻。奧瑪爾·海亞姆的傑出還在於,他當時已經發現三次方程具有不止一個根,並且證明了另一個根的存在。他寄語後來人說到:“也許我們之後的人們會解決這個問題。”這一期望後來在16世紀由三位義大利人——費爾羅(del Ferro,1465~1526年)、塔塔利亞(Tartaglia,1499~1557年)與斐拉裡(Ferrari,1522~1565年)變為現實,他們找到瞭解所有三個根的一般方法。另外,奧瑪爾·海亞姆還進一步發展了二項式定理。
在希臘數學中,“數”的概念一般僅僅擴展到簡單的加法和乘法運算,然而從算數運算到代數的飛躍,使人類第一次生長出在一切自然科學領空飛翔的翅膀……
阿拉伯人金迪(al’Kindi,西元801~873年)是那個時代的科學多面手,還是在算術學方面頗有造詣的數學家,並且寫了許多這方面的著作,涉及範圍包括印度(阿拉伯)數位、調和數、數位排列、相對值、比例、數位的處理與相消或相約,以及用有窮證明無窮等。在幾何學方面,金迪擅長于平行理論的研究,他甚至給出一條(數學)引理以證明或否定某種可能性——即在同一平面上的數條直線,既非平行,也不相交。金迪還寫了兩本關於光幾何學的書籍。根據1987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發現的蘇萊曼時期的奧斯曼帝國的檔案,金迪也是迄今已知的最早的(根據字母的使用頻率)破譯密碼的專家,可謂密碼分析學或密碼破譯學的鼻祖。金迪的手稿英譯名為“On Deciphering Cryptographic Messages”(《密碼資訊的破解》)。
塔比特(Thabit ibn Qurrah,西元826~901年,兼物理學家)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數學家,他在數學方面的地位主要在於,將數的概念擴展到實數,提出“積分”,建立了某些球面三角學及“解析幾何”定理。他在西元850年左右寫了一本書——《互滿數的確定》,揭示了建立“互滿數”的一般數學方法。
阿拉伯帝國的穆斯林對於數學的另一巨大貢獻是三角學(三角函數),其學術思想可能主要來源於印度與希臘的三角學知識。三角學是隨著一些探究宇宙奧秘的科學家在觀測天體運行與研究天文曆算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眾所周知,研究天文演變的規律離不開三角學或數學知識,所以作為天文學家的最重要條件是,首先他必須是一位數學家。
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的巴塔尼(al’Battani,歐洲人也稱作Albatenius,西元850~929年)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天文學家與數學家。他完成了三角學的建立與系統化工作。在從事天文學研究的過程中,巴塔尼首先系統性地創建了三角學即三角函數這一數學分支的許多重要概念,如正弦、余弦、正切、餘切。我們今天在中學學習的一些三角函數公式就是巴塔尼提出的;另外,關於球面三角形的余弦定理也是這位數學家對人類的貢獻。而正割與余割的概念則是阿拉伯帝國的另一數學家兼天文學家瓦法(al‘Wafa,也稱Albuzjani,西元940~998年)建立的,瓦法還指出正弦理論也可以運用在球面幾何學上。
2、天文學
阿拉伯帝國的科學家們對天文學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在哈裡發馬蒙執政時期(西元813~833年),他們已經能夠嫺熟地運用諸如星盤、等高儀、象限儀、日晷儀、天球儀和地球儀之類的天文儀器從事天文學研究。
前文提及的巴塔尼(al’Battani,歐洲人也稱作Albatenius,西元850~929年)是對歐洲影響最大的天文學家。他的《天文論著》(又名《星的科學》)頗具學術價值,後來的一大批天文學家諸如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年)、第穀(Tycho,1546~1601年)、開普勒(Kepler,1571~1630年)、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年)等人,無不研習巴塔尼的著作並受益非淺。他所創制的天文曆表——《薩比天文》,一直是其後幾個世紀歐洲天文學家的基本讀物。
巴塔尼出生于美索不達米亞的哈蘭(位於今土耳其東南部)的一個崇拜星辰的塞比教派家庭,這恐怕與其日後對天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以及學習製作天文儀器的技能不無影響;但是他本人則是虔誠的穆斯林。巴塔尼的工作主要是在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著名的安條克(位於今土耳其境內)與拉卡(位於今敘利亞境內)天文臺完成的。
這位偉大的天文學家的主要成就在於,他不僅編錄了489顆天體,而且把一年的時間長度精確至365天5小時48分24秒,重新計算出(春秋二分點的)分點歲差為54.5‘,以及測定黃赤交角(赤道平面與黃道平面的交角)為23度35分(現在已知數值為23度26分)。它們比托勒密(Ptolemy,西元2世紀)的《天文學大成》的描述更為準確。巴塔尼提出地球在一條變動著的橢圓形軌道上運動(偏心率),發現太陽遠地點的“進動”(即太陽距離地球最遠點的位置是變化的,這是巴塔尼最著名的發現),以及認為日環食可能是一種日全食。他對於太陽運行的觀測比哥白尼還要精確,並且在幾個世紀之後還被上述歐洲的天文學家所採用。
巴塔尼的《天文論著》於1116年由義大利提沃利的普拉托(Plato,11~12世紀)譯成拉丁語。
蘇菲(al’Sufi,西元903~986年)所著《恒星圖像》(或譯作《恒星星座》),一書,是伊斯蘭天文學觀測的三大傑作之一。蘇菲根據自己的實際觀測,在書中確定了48顆恒星的位置、星等和顏色,並且繪製出精美的星圖與列有恒星的黃經、黃緯及星等的星表。他還為許多天體進行了名稱鑒定,提出許多天文術語,許多現在世界上通用的天體名稱都來源於蘇菲的命名,例如牽牛星、畢宿五、天津四等。蘇菲的星圖也是關於恒星亮度的珍貴的早期資料。西元964年,正是他最早記錄下仙女星座。這位的天文學家對天文學界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例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蘇菲星團”,國際天文學會還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月球表面一處環形山來紀念他。
前文提及的瓦法(al‘Wafa,也稱Albuzjani,西元940~998年)是巴格達天文學派最後一位著名人物。已知他曾測定過黃赤交角和分至點,並且是提出“月球出差”的第一位天文學家;此外他還為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編撰了簡編本。
奧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西元1048~1131年)在當時由突厥塞爾柱王朝管轄的伊斯法罕,參與並領導了天文曆表的編撰與曆法改革工作,制定的賈拉利曆的精確程度已經十分接近格利高裡曆,根據這部曆法測定一天的長度為365.24219858156天(後來由於政局的動盪曆法改革工作被迫終止)。
比魯尼(Biruni,西元973~1050年)堪稱那個時代理論水準與實踐能力俱佳的“天才”,天文學(與數學)是其深入涉足的領域。他在一部近1500頁的著名的百科全書——《馬蘇迪之典》中,測定了太陽遠地點的運動,並且首次指出其與歲差變化存在略微的差別。《馬蘇迪之典》是一部集天文、地理和民族學的通科著作。比魯尼還設想地球是自轉的。他在寫給好友、同時代的著名醫學家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稱為阿維森納Avicenna,西元980~1037年)的信中,甚至提出地球繞太陽運轉的學說,並且認為行星的軌道是橢圓形而非圓形的。地球繞太陽運轉的觀點還表現在比魯尼的一部天文學百科全書——《占星入門解答》之中。他說,如果認為地球是在圍繞太陽運轉的話,那麼就不難解釋其他星體的運動情況。另外,至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銀河系,比魯尼發現它是由“無數的各種星體組合而成”。
其實,比魯尼是一位勤奮、多產、涉獵範圍廣博的科學家,他一生寫作了涵蓋20多門學科的大約146部著作(只有22部傳世),其中多數是與數學及天文學有關的,例如《投影》。
在法提瑪王朝(西元909~1171年,中國史書稱“綠衣大食”)哈裡發哈基姆(al’Hakim)統治時期(西元966~1020年),天文學家尤努斯(也譯作尤尼,ibn Yunus,西元950?~1009年)在參考200多年以來天文觀測資料的基礎之上完成了《哈基姆星表》(也譯作《哈基姆歷數書》),並還用正交投影的方法解決了許多球面三角函數問題。尤努斯的傑出在於,他的計算細緻而精准,例如,他注意到投向地平線的光線的折射所引起的誤差,並且首次給出被觀測物體的40分差角。他對月食的觀測記錄是極其可靠與可信的,其30次月食報告為近、現代天文學家,例如西蒙•;紐科姆(Simon Newcomb,1835~1909年),研究月球的長期加速度提供了珍貴的天文資料。
穆斯林的信仰要求禮拜的定時,而這與太陽與月亮或其它天體的運動是密切相關的。尤努斯就是一位可以給出精確時間的天文學家,而且他的天文曆表可以在伊斯蘭曆、科普特曆(一種古代埃及人使用的曆法)、古敘利亞及波斯曆之間進行轉換或換算,以方便人們的使用。
1080年,西班牙穆斯林天文學查爾卡利(al’Zarqali,西方人稱為Arzachel,11世紀)完成《托萊多星表》(也譯作《托萊多天文表》),其中有天文儀器(尤其是阿拉伯人擅長的儀器——星盤)的結構介紹與使用方法。《托萊多星表》對托勒密體系進行了修正,以一個橢圓形的“均輪”代替“本輪”。另外,《天文表》也是查爾卡利的傑作。
在對於宇宙體系的認識上,穆斯林天文學家質疑托勒密的本輪學說,並試圖建立一個真正的宇宙體系。
先後經歷過阿拔斯王朝與蒙古人建立的伊爾汗國兩個時代的天文學家(兼數學家)圖西(al’Tusi,1201~1274年),不僅建立了月球的運動模型,而且還在1247年提出所謂的“圖西力偶”定理(即線性運動可以由圓周勻速運動演化而成,反之亦然)。科學史學家喬治·薩里巴(George Saliba,1939~)在評價“圖西力偶”定理時說:“如果僅靠歐幾裡得(Euclid,約西元前3世紀)的《幾何原本》和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等古希臘的數學和天文著作中所提供的數學資訊,哥白尼天文學的數學大廈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來。構建這一大廈所需要的,實際上也是哥白尼本人所利用的,是兩種新的數學原理。而這兩種數學原理卻都是在哥白尼以前大約300年間發現的,並為伊斯蘭世界的天文學家們明確地用來改進希臘天文學。”文中所提到的數學原理之一,便是圖西的“圖西力偶”定理,它在16世紀初被哥白尼採用。
圖西一生寫作了關於天文、數學(幾何與三角學)、物理、哲學、倫理學及邏輯學等學科的100多部著作,甚至還整理過伊本·西那的《醫典》,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伊爾汗天文表》(或譯作《伊爾汗歷數書》)。
位於今伊朗境內的、聞名遐邇的馬拉蓋天文臺也是在圖西倡議下建立于伊爾汗國初期,其天文儀器甚至在當時被帶到中國的元大都。馬拉蓋天文臺的遺跡至今尚存,成為人類文化遺產。
喬治·薩里巴在談及阿拉伯帝國天文學與哥白尼天文學關係的時候說道:“當我們想到哥白尼天文學本身給我們帶來的所謂‘哥白尼革命’這樣的概念時……我們便不難想像到哥白尼的數學天文學與在他以前用阿拉伯語寫作的天文學家們之間的交融了。或者換句話說,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阿拉伯天文學與哥白尼天文學之間的模糊邊界會是這樣有趣了。”
凱文·克裡斯納斯(Kevin Krisciunas)則對某些蓄意抹殺伊斯蘭天文學成就的態度給予直率的批評。他在《世界天文學中心》一書第二章的開頭即寫到:“那種認為在托勒密之後,天文學研究陷入沉睡直到哥白尼時代才得以蘇醒的看法,是一常見的錯覺……那些認為阿拉伯人沒有做出自己的貢獻的人們,對於這一學科並未進行過調查研究。”他還進一步指出,中世紀的天文學家的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用阿拉伯語書寫科學著作的,即使是猶太人與基督徒也莫不如此。
事實上,阿拉伯帝國天文學在今天已經落下永久的烙印,甚至現在人們使用的很多與天文有關的詞彙,諸如“azimuth”(地平經度、方位角)、“nadir”(天底)、“zenith”(天頂),等等,都是源自阿拉伯語。
可以肯定地講,阿拉伯帝國的天文學家對於宇宙天體的認識,是人類天文學史上由托勒密到哥白尼之間最重要的銜接。
3、醫藥學
阿拉伯帝國在醫學上取得了相當出色的成果。
拉齊(al’Razi,歐洲人稱其為Rhazes,西元865~925?年)不但是一位傑出的化學家與哲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醫學家。他學識深邃而廣泛,一生寫作了200多部書,尤以醫學(與化學)方面的著作影響巨大。拉齊曾先後擔任雷伊(位於伊朗德黑蘭附近)和巴格達醫院院長,並從事學術著述,被譽為“阿拉伯的蓋倫”、“穆斯林醫學之父”。
拉齊在醫學上廣泛吸收希臘、印度、波斯、阿拉伯(甚至中國)的醫學成果,並且創立了新的醫療體系與方法。他尤其在外科學(例如疝氣、腎與膀胱結石、痔瘡、關節疾病等)、兒科學(例如小兒痢疾)、傳染病及疑難雜症方面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與理論知識。他是外科串線法、絲線止血和內科精神治療法的發明者,也是首創外科縫合的腸線及用酒精“消毒”的醫學家,還是世界上早期準確描述並鑒別天花與麻疹者(中國人認為中國的葛洪是最早描述天花症狀的,在拉齊之前也有一位阿拉伯帝國的學者介紹過天花與麻疹,但拉齊的論述更為後人所瞭解),並且將它們歸入兒科疾病範疇。拉齊注意到一種疾病出現的面部浮腫和卡他症狀(如打噴嚏、流清涕),與玫瑰花生長及開放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他第一個指出所謂的花粉熱就是緣於這種玫瑰花的“芳香”。
拉齊的代表作《曼蘇爾醫書》是醫學史上的經典著作。他於西元903年把《曼蘇爾醫書》捐獻給薩曼尼德的王子兼雷伊地區長官曼蘇爾。《醫學集成》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醫學著作,作者花費15年的時間完成此書。《醫學集成》主要講述的是疾病、疾病進展與治療效果。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保存有一部《醫學集成》的阿拉伯語手抄本,它是在1094年由一位佚名抄寫人抄寫的,也是該館最古老的醫學藏書。
《曼蘇爾醫書》和《醫學集成》分別於1187年與1279年在西班牙深受穆斯林文化影響的歷史名城托萊多與法國的安茹被譯成拉丁語而在歐洲廣泛傳播,並且隨即取代了蓋倫(Galen,西元130?~200?年)的醫書;它們在文藝復興時期又被多次翻印,並且由當時著名醫學家加以注解。
此外他還著有《醫學入門》、《醫學止境》、《精神病學》、《天花與麻疹》、《藥物學》、《蓋倫醫學書的疑點和矛盾》等。
拉齊確信,他在科學上取得的成就一定會被比他卓越的思想超越。在他看來,那些有志於科學研究的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因為這是科學發展的規律。
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稱為阿維森納Avicenna,西元980~1037年)西元980年出生於中亞的歷史名城布哈拉附近,是代表阿拉伯帝國醫學最高境界的里程碑。他與希臘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西元前460?~370?年)、蓋倫並稱醫學史上的三位鼻祖,被尊為“醫者之尊”(“Doctor of Doctors”)。伊本·西那學識淵博,除了醫學之外,他在其它方面也頗有造詣。
伊本·西那的醫學成就主要體現於一部極其著名的百萬字醫學百科全書——《醫典》。他在《醫典》的開篇中說:“醫學是這樣一門科學,它告訴人們關於機體的健康狀況,從而使人們在擁有健康的時候珍惜健康,並且幫助人們在失去健康的時候恢復健康。”《醫典》一書全面而系統,全書包括5部分,分別講述醫學總論、藥物學、人體疾病各論及全身性疾病等內容。
感染性疾病曾經一直是人類疾病的第一位死亡原因,今天人們已經認識到,這類疾病是由病原體例如致病性細菌、真菌與病毒等引起的。伊本·西那提出人本身以外的因素在引發疾病方面的作用,首先發現了“原體”可以是產生疾病的原因,指出肺結核就屬於此類疾病,天花和麻疹也是由肉眼看不到的“原體”所致,而且還強調了“消毒”的重要性。他發現水與土壤可以是傳播致病物質的媒介。伊本·西那不但認識到鉤蟲病是由腸道寄生蟲引起的,並能夠做出準確的診斷。
他主張外科醫生應該在早期階段治療惡性腫瘤,以確保對所有病變組織加以切除。伊本·西那在著作裡強調膳食營養的重要意義,提出氣候和環境與疾病有關的觀點。他研究過心臟瓣膜,發現主動脈有三個瓣膜,瓣膜的張開與關閉配合心臟的收縮與舒張,從而維持血液的流出與流入。伊本·西那描述和記錄了有關心臟病藥物的提煉及皮膚病、性病、神經病(例如腦膜炎)與精神疾病等病症。他還能夠將縱膈炎與胸膜炎相鑒別。他也介紹了用燒灼治瘋狗咬傷、針刺放血與竹筒灌腸以及音樂等療法。
伊本·西那主張,在正式推廣使用一種新藥之前,首先應該進行動物與人體實驗,從而保證藥物的安全性。
《醫典》從12世紀被譯成拉丁文起直至17世紀的數百年間,始終被歐洲的醫學院校用作醫學教科書,僅在15世紀的最後30年內,這部著作就被用拉丁文出版過15個版次。它對西方醫學的影響勝過任何一部醫學著作。著名醫學教育家奧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年)博士對《醫典》的評價是“被當作醫學聖經的時間比其它任何著作都要長”。《醫典》是現代醫學產生的重要基礎之一。
其實,伊本·西那的研究範圍非常廣泛,他一生大約寫了450部著作,它們不僅是關於醫學的,還有專門論述哲學、心理學、地質學、數學、天文學、邏輯學與音樂等學科的,其中傳世的有240部左右(關於哲學與醫學的分別為150部與40部)。例如影響力僅次於《醫典》的《治療論》一書,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書。
出於對兩位醫學先驅的尊敬,拉齊與伊本·西那的畫像今天仍然懸掛在巴黎大學醫學院的畫廊上。
西元10世紀的紮哈拉維(Abul Qasim al’Zahrawi,歐洲人稱之為Abuicasis或Albucasis,阿爾布凱西斯,西元936~1013年)是出生在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的著名醫學家,享有“外科學之父”的讚譽,其祖先來源於阿拉伯半島的安薩爾部落。
紮哈拉維的《醫學手冊》是一部集其數十年醫學知識與經驗的著作,包括30篇的內容,涵蓋大量臨床問題,適用于執業醫生與醫學生。這部著作附有歷史上最早的外科器械插圖與文字說明,而且數量相當豐富(200幅左右)。這些精緻的插圖(與文字說明)使其極具學術價值。他還把外科治療劃分成幾個部分,例如燒灼術、手術切除、放血療法與接骨術。12世紀,《醫學手冊》的外科部分(第30篇)在托萊多被來自義大利克雷默那的翻譯家傑拉德(Gerard,1114~1187年)翻譯成拉丁語,並且在1497~1544年之間至少再版10次之多。從12~15或16世紀,幾乎歐洲所有的醫學家編撰的外科教科書無不參考或引用紮哈拉維原書的譯本,例如Roger、Guglielmo Salicefte、Lanfranchi、Henri de Mondeville、Mondinus、Bruno、Guy de Chaulliac、Valescus、Nicholas及Leonardo da Bertapagatie等人。
紮哈拉維不僅改進了一些器械,還發明了許多外科器械,例如一種引流腹腔積液的斜面套管,插入尿道治療尿路結石的探頭,以及一種用於切開膿腫的隱蔽式手術刀。他還發明、引進了鑷子、(羊)腸線以及今天婦產科醫生使用的窺陰器與擴陰器等。
在《醫學手冊》的第一與第二篇裡,紮哈拉維歸類了325種疾病,討論了它們的症狀與治療,並且在第145頁上首次描述了一種由“健康”母親傳遞給兒子的出血性疾病,也就是現代醫學所說的血友病。這部分篇幅後來亦有拉丁文譯本出現,名為“Liber Thoricae”。
在婦產科方面,紮哈拉維的著作包括指導訓練助產士如何處理異常分娩,取出死胎與去除胎盤,以及剖腹產的實施方法等。
紮哈拉維對於後來的醫學尤其是外科學具有很大的影響,人們也並沒有忘記這位生活在1000年前醫學家。現在,在紮哈拉維的家鄉西班牙科爾多瓦,有一條叫做“Calle Albucasis”的街道,就是以他的拉丁化名字Albucasis命名的,意思是“阿爾布凱西斯(紮哈拉維)大街”;西班牙旅遊局在這條街道的6號建築物門前安放了一塊銅匾,上書“阿布·凱西姆舊居”(“阿布·凱西姆”也是紮哈拉維的名字,取自其全名)。按紮哈拉維的設計而復原的外科器械,曾經在西班牙、突尼斯和巴基斯坦等地的博物館中莊重地陳列展示,以表達人們對他的尊敬。
另一位出生在西班牙的醫學家伊本·拉希德[ibn Rushd,拉丁名阿威羅伊(Averroes),1126~1198年]是研究組織學的先驅,他還發現患過天花的人以後不會沾染天花,他對血管與運動保健也頗有研究,西班牙與北非的摩洛哥都曾留下他工作的足跡。他的《醫學原理》在當時是一部很全面的醫學入門書籍。
除了醫學之外,哲學與天文學也是伊本·拉希德研究的物件,尤其是在哲學方面,他的“阿威羅伊哲學”(Averroism)對西方學術界的影響力甚至大大勝過其在伊斯蘭世界所享有的威望。
阿拉伯帝國的醫學非常注重眼科疾病,醫生們好像大多都對這方面的病症顯示出濃厚的興趣,而且具有很高的診斷與治療眼科疾病的技藝。幾乎所有的醫學著作都有專門的篇章論述眼科疾病,但是最全面的關於眼科疾病的論述是以專著的形式講述的。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西元809~873年,歐洲人稱之為Joannitius,兼翻譯家與數學家,基督徒)寫了多部眼科學專著,諸如《眼科問題》、《眼睛的結構》、《五彩斑斕》、《眼科疾病》、《眼病治療》、《眼科疾病的手術療法》……其中以《眼科十論》影響最大。
卡哈爾(Kahhal,西元940~ 1010年,可能是基督徒)則在其眼科學專著《眼科醫師手冊》裡介紹了多達130種眼科疾病。
白內障是一種常見的眼科疾病,其病變部位在眼球的晶狀體,未治者的結局常常是致盲。當時,聰明的醫生已經知道它的治療方法。與卡哈爾同時代的毛斯裡(Mawsili),是白內障針吸術的發明者,這種技術即通過一種金屬空心針經過鞏膜吸除白內障病變。200多年後,即大約於1230年,有一位歷史學家兼眼科醫生在大馬士革的一家醫院裡親眼目睹過使用上述器械去除白內障的手術的過程。然而,14世紀埃及著名的眼科醫生薩達卡(Sadaqah)對這種療法的真實性表示質疑。
沙眼是又一眼科常見疾病,常引起倒睫、瞼內翻及角膜血管翳,嚴重者也可致盲。當時的醫生對於此症已有深刻的認識,他們不但對角膜血管翳給予清晰的描述,而且尤其擅長於手術切除這種長在角膜上的血管組織,但是這種手術的真實性似乎令人疑惑。他們在手術中使用一系列自己發明的手術器械,例如開眼器、拉鉤、細小的手術刀和撥針。他們還能夠採用類似的手術器械治療翼狀胬肉。
以當時的醫學水準來看,上述手術是非常精細與複雜的,而且患者往往要忍受相當程度的疼痛,故帝國的醫生可能並非常規進行這種手術。
在12~14世紀,在阿拉伯帝國範圍內出現了許多眼科學著作,例如《眼科指南》與《眼科疾病治療的思考》等,後者分17章講述了眼的解剖、生理,以及124種眼科疾病的病因、症狀和治療,其中不乏在作者之前從未描述過的內容。它們在當時以及其後幾百年間都是從醫者學習眼科疾病的權威著作。
雖然眼科疾病早先一般是在外科疾病中討論的,但是阿拉伯帝國的醫生已經開始把眼科疾病從一般醫學中獨立出來,這就是現代眼科學學科的雛形。例如13世紀敘利亞醫學家庫弗(Quff,西元1233~1286年)在其編寫的外科專用手冊裡,故意不收入任何眼科疾病,因為在他看來,眼部疾病應該屬於專科醫生的診治範疇。
哈森(al’Haitham或al’Haytham,西元965~1040年,歐洲人稱為Alhazen)不僅是物理學家、天文學家與數學家,他在研究光學原理的同時,也對人類眼科學或眼科生理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研究豐富了人們對於眼球的生理解剖和視覺原理的認識。今天眼科醫生使用的“視網膜”、“角膜”、“玻璃體”及“前房液”等專業術語大多與哈森有關。
穆斯林是研究精神疾病的開拓者,而且在這一領域發揮了早期的作用。事實上這歸功於拉齊的直接貢獻,是他在巴格達為精神疾病患者建立了特別的病房。正如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醫學教授賽義德(Ibrahim B. Syed)所言,穆斯林為“精神病學帶來一種冷靜的全新的意識”。因為穆斯林醫學家根本不會相信在歐洲基督教世界盛行的精神疾病的“鬼魂學說”(鬼魂附體),所以他們能夠對此類疾病進行冷靜的臨床觀察。
13世紀大馬士革的醫學家納菲(或稱伊本·那非斯,ibn al’Nafis,1213~1288年)對蓋侖的血液迴圈學說進行了積極的批判。蓋侖認為血液的流程是右心室→左心室,而納菲發現心臟左右心室之間的隔膜很厚,而且隔膜上面沒有像蓋倫所設想的那種孔道,血液不可能從右心室直接流至左心室。為了糾正蓋侖的謬誤,納菲提出一種血液小迴圈(肺循環)理論,即血液在此的流程是右心室→肺動脈→肺(交換空氣)→肺靜脈→左心(房)室。這種血液小迴圈理論比後來的塞爾維特(Servetus,1511~1553年,因蔑視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學說被宗教裁判所裁決處死)的發現要早300多年。遺憾的是他的學說並未在當時引起人們的重視,被淹沒了700多年直至20世紀才重新被後人在佈滿塵埃的檔案中發現。另外,1547年,安德里亞·阿爾帕戈(Andrea Alpago)曾經將伊本·納菲的一些書稿翻譯成拉丁語,因此歐洲人完全有條件瞭解伊本·納菲的重要工作(甚至包括直接閱讀阿拉伯語書稿),而就在這前後歐洲的醫學家便獲得了與伊本·納菲相同的“發現”。難道這只是巧合?以下是納菲手稿的英譯。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of the heart must arrive at the left chamber, but there is no direct pathway between them. The thick septum of the heart is not perforated and does not have visible pores as some people thought or invisible pores as Galen thought. The blood from the right chamber must flow through the vena arteriosa (pulmonary artery) to the lungs, spread through its substance, be mingled with air, pass through the arteria venosa (Pulmonary vein) to reach the left chamber of the heart……the nourishment of the heart is from the blood that goes through the vessels that permeate the body of the heart……”
伊本·納菲不僅正確揭示了肺的解剖結構,而且還是第一位記錄心臟冠狀動脈血液迴圈的醫學家。他寫到“……心臟的營養物質來自沿這些血管運行的血液,而這些血管是分佈於心臟的……”
除了前述的一些醫學專論之外,阿拉伯帝國的一些醫學家還寫作了很多關於特殊疾病及相關藥物的著作。例如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的兒子,易司哈格·伊本·侯奈因(Ishaq ibn Hunayn,西元?~910年)的介紹治療健忘症藥物的《健忘症治療藥物》、卡塔尼(Kattani,西元951~1029年)的關於治療體表疾病的《體表危險疾病的治療》。賈紮爾(Jazzar,西元895~980年)不僅專為旅行者寫了一本介紹疾病、發熱、有毒昆蟲與動物叮咬,以及在沒有醫生的情況下如何治療與處置此類病症的書籍(拉丁版名為“Viaticum Peregrinantis”),而且作為一名虔誠的穆斯林,他還非常熱心於貧困人口的求醫問藥問題,《窮人醫藥》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此外,有一位猶太醫生(拉丁名為Maimonides,1135~1204年)發表了一本介紹痔瘡的小冊子,一位11世紀的基督徒巴特蘭(Butlan)還寫了一本治療修道士疾病的書籍。它們都是用阿拉伯語書寫的。
關於從醫者的職業操守,(伊斯蘭哲學家、宗教學者)伊本•;哈茲姆(ibn Hazm,西元994~1064年)提出,一個做醫師的人必須在道德上具有良好的品質,即仁慈、富有同情心、友善、忍辱、接受負面批評;他對醫師外表的要求是,醫師應該留短髮,勤剪指甲,穿戴乾淨,舉止尊嚴。
在藥物學方面,阿拉伯帝國的醫生與藥物學家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與大量的創新。他們善於使用複方製劑,主藥、佐藥與替代藥巧妙搭配,首先開始將樟腦、氯化氨與番瀉葉等作為藥物加以使用;在他們的處方裡,還出現了來自中國、東南亞、喜馬拉雅山脈以及非洲的藥物;而糖漿、軟膏、搽劑、油劑、乳劑或脂等劑型,以及丸藥的金、銀箔外衣則是他們首創的,甚至今天西方醫學界使用的“Syrup”(糖漿)、“Soda”(蘇打)等詞彙,都是從阿拉伯語音譯的。當時的醫學百科全書或綜合性醫學書籍都留有專門的章節介紹藥物以及處方藥物的搭配。這部分章節系統地講解了藥物與處方的構成成分與配製的程式和步驟。
伊本·貝塔爾(ibn al’Baitar,1188?~1248年)是中世紀最偉大的藥用植物學家,他編寫了兩部醫藥學著作《藥物學集成》與《醫方彙編》,堪稱經典之作,其中藥物是根據它們的治療作用進行編排的,而且除了阿拉伯語名稱之外,還加上了希臘語和拉丁語名稱,從而促進了醫藥學知識在歐洲的傳播。《醫方彙編》的拉丁語譯本的若干部分,1758年還曾在義大利的克雷默那出版。
穆斯林的藥物學成就對歐洲具有不可或缺的影響,後來相當長時期內歐洲這方面的著作,主要就是在先前穆斯林著作的基礎上編輯或是稍做改編而成的,例如約翰尼斯1250年完成的《Expositio Supra Nicolai Antidotarium》(分別於1495、1599和1602年在威尼斯出版)。阿爾巴諾(1306~1316在帕多瓦任教)的《Conciliator and De Venenorum Remediis》則是廣泛承襲伊本·拉希德等人的著述。15世紀薩拉迪尼·阿斯柯洛的《Compendium Aromatariorum》(藥劑師手冊),在形式和內容上深受穆斯林醫學家伊本·西那等人的影響。而17世紀晚期出版的《倫敦藥典》,在編列的藥物分類和劑型種類上也反映出受到穆斯林藥物學影響的程度。事實上,歐洲人使用的藥典一直依賴穆斯林的著作與資料,直至19世紀晚期。
在眾多科學學科中,醫藥學是穆斯林的長處所在,這種地位的取得,與學科教育是分不開的,而早在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初期,即西元765年,巴格達就建立了醫科學校培養醫藥學人才。
阿拉伯帝國早在倭馬亞王朝時期(中國史書稱為“白衣大食”,西元661~750年)就在大馬士革建立醫院提供醫療方面的服務,但是有文獻可考的世界上第一所正規醫院是西元9世紀在阿拔斯王朝的巴格達建立的;大約經過一個世紀的時間,又有5所醫院在巴格達開業。而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初期醫院,則是東征的十字軍在伊斯蘭世界開闊眼界之後,返回歐洲13世紀在巴黎建立的,與巴格達的醫院相差約有400年的時間……西元931年,帝國還規定城市或醫院的醫生必須通過考試才可以開業行醫(據說先前的羅馬帝國也有城市醫生需要通過考試的規定)。根據記述,西元10世紀初期那裡已經建立起流動醫院,日常在帝國的村莊提供醫療服務。巴格達最具規模的一所醫院建立於西元982年,該院建院之初就擁有包括眼科醫生與外科醫生(含正骨醫師)在內的25名醫生,而到1184年,一位旅行家描述說,那所醫院的規模就像是一個巨型的宮殿。
西元872年帝國在開羅建立的一所醫院,它是迄今最早的為精神病患者提供醫療的醫院;12世紀與13世紀,納斯裡醫院和曼蘇裡醫院先後在開羅建立。另外,努裡醫院是12世紀在大馬士革建立的。
相對而言,在穆斯林管理下的西班牙,醫院出現的比較晚一些。
帝國的醫院在設計上即為其賦予了非常完善的功能。目前瞭解比較多的是關於西元12~13世紀敘利亞與埃及的醫院的情況。那裡的醫院在佈局上呈縱橫交叉垂直形狀,中央部分是4個拱形大廳,比鄰有藥房、儲藏間、圖書室、工作人員生活區以及廚房,每個拱形大廳都有噴水池提供乾淨的水源。不同的疾病,諸如胃腸道疾病尤其是痢疾與腹瀉、風濕性疾病、外科疾病、眼科疾病和發熱等各自在不同的區域就診,而女性患者則是在獨立的診室與病房就診的。醫院還為精神病開闢專門的病房。醫院不僅配置正常的執業醫生與藥劑師,而且安排有值班醫生接診預約定時複診的病人。當時的醫院同時具有醫學教學功能,並且有管理、護理與勤務人員從事工作,還有醫學生為非專業人員提供相應的培訓。
所有醫院的建立與運營在財政上主要依靠的是國家預算,這筆預算來源於國家(向富人)徵收的遺產稅;另外,富人與統治者的捐贈也為醫院提供了資金(伊斯蘭教教義要求,生活寬餘者,應該用部分節餘説明窮人,給予的可以是實物也可以是金錢,即交納“天課”)。雖然獨立的行醫者是收取一定的費用的,但是醫院的服務據說是免費的。
4、化學
除了在數學、天文學和醫學等學科收穫頗豐之外,阿拉伯帝國的學者還是化學這一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其中哈揚(Jabir ibn Hayyan,西元721?~803年,歐洲人也稱之為Geber)與前文提及的拉齊(al’Razi,歐洲人稱其為Rhazes,西元865~925?年)被認為是“化學之父”。
化學源自煉金術,據說埃及法老時期就產生煉金術了,中國的煉丹術與之有一定關係。西元7世紀,上述技術與古希臘思想相融合而形成阿拉伯煉金術及阿拉伯化學。阿拉伯煉金術及阿拉伯化學後來傳入歐洲,逐步演進為近、現代化學。
哈揚在化學實驗中確立了實驗法的重要地位。他不但首先發現幾種化合物,還掌握一些化學物質的製備技術,例如製備硫化汞與五氧化二砷,製備近乎純淨的硫酸鹽或明礬、堿等化合物,使用酸來溶解某些惰性金屬如金、銀,以及精通金屬冶煉包括黃金提煉術。此外,他還通曉製作染布與皮革的染料與防水布的防水塗料,製造一種可以阻燃的紙,以及在夜晚看得到的墨水。我們現在仍在使用的一些化學術語例如“堿”,就是這位化學家發明的。
儘管他有時被當作一名煉金術士,然而他似乎不太熱衷於制取貴重金屬(將“賤”金屬轉化為“貴”金屬是通常的煉金術士所追求的),取而代之的是,他努力開創基礎性的化學方法以及研究化學反應本身具有的內在機制,從而將化學從煉金術發展成一門科學。他強調在化學反應過程中,各種參與反應的物質的量是一定的,這或可被看成是“定比定律”的雛形。
據信他一生寫作了約100多部論著,在這些著作中約有22部是關於化學與“煉金術”的。它們被翻譯成包括拉丁文在內的多種歐洲語言在歐洲的大學裡講授。譯成英語的就有《Book of Kingdom》、《Book of Balances》及《Book of Eastern Mercury》等。許多哈揚(及其它化學家)的著作當時是不署名的,因此人們無法準確地估計其數目。17世紀英國翻譯家裡查德•;拉塞爾(Richard Russell)認為,英譯名為《Sum of Perfection》的著作的作者就是哈揚。
不過在哈揚之後,據說也有一些他人的文稿假託哈揚之名。
雖然在哈揚的某些著作中體現的宗教與哲學觀點業已受到批判,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哈揚的主要貢獻在於化學領域而非宗教與哲學。他在化學領域的各種開創性成就——首次制取各種酸,尤其是硝酸、鹽酸、檸檬酸、酒石酸,以及對於實驗法系統性的強調,這些都是非常卓越的。他對化學的基礎性貢獻包括發明一些科學的化學實驗方法,諸如蒸餾、結晶、煆燒、昇華、蒸發等,以及一系列與之相應的實驗儀器和設備。哈揚之所以被公正地看成是現代化學之父,正是基於他這些卓越的工作。因此,德國的梅耶哈夫教授說,歐洲化學的發展可以直接追溯到哈揚。
拉齊不僅是醫學家,而且還是享有盛名的化學家。他繼承了前者的煉金術理論及化學實驗的傳統,並與藥物學研究相結合,使得化學理論和實驗法繼續發展。他在《秘典》(又譯《煉金術的秘密》或《秘密的秘密》)一書中首先確定許多化學概念,把已知的物質分為四大類:植物、動物、礦物和衍生物,同時介紹了物質的“原子”構成學說並講解了煉金術的原理,還對化學實驗儀器與使用方法做了詳細的記載。拉齊的《秘典》記載了化學反應步驟以及他本人從事的一些化學實驗,這些實驗包括蒸餾、煆燒和結晶等內容。拉齊的一些具有創新性的實驗在《秘典》中都有反映,包括熔解金屬的方法、水銀的昇華、苛性鈉的制取、白降汞溶液的使用,以及從橄欖油制取甘油等。希爾指出,拉齊的《秘典》猶如一部實驗指南的雛形。在拉齊的實驗室裡有許多今天仍然使用的實驗設備,例如坩堝、分流器、蒸餾瓶、曲頸瓶、帶有導管的蒸餾塞以及各種類型的加熱爐等。
阿拉伯帝國的一大批學者乃至從業者在許多技術發明創新方面顯示了無窮的才能與智慧,他們已經掌握了在當時算是獨一無二的化學技術。而由傑拉德(Gerard,西元1114~1187年)12世紀在西班牙托萊多翻譯的一部穆斯林學者的書籍(譯作“De Aluminibus”),則講述了氯化汞的合成步驟。他們還將化學知識應用於生產與製造,例如當時的制革以及玻璃、墨水、油漆、染料、焊料、粘合劑和人造珍珠等的加工和制糖等,其中許多東西與後來的工業具有直接的關聯;他們將含糖與澱粉的物質發酵後通過蒸餾的方法制取酒精,比歐洲人早了300多年。今天人們使用的“alchemy”(煉金術)和“alcohol”(酒精)等詞彙,都是取自他們的發明,而“chemistry”(化學)一詞則是去掉“alchemy”的詞頭“al”之後衍生出來的。他們還發明了肥皂的製作方法。肥皂一詞阿拉伯語讀作“shabun”,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的肥皂(sabon),甚至法語的肥皂(savon),都是來自阿拉伯語,依此類推,英語的肥皂(soap)和洗髮香波(shampoo)來源也大致若此……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另外,學者們開展化學實驗的同時也帶動了製藥水準的提高。
亨利·萊斯特評價說:“在實用方面,他們(穆斯林——筆者注)發現了鹵砂(氯化銨),制出了苛性鹼,認識到動物性物質的特性和它們在化學上的重要作用。他們對礦物性物質的分類,已成為後世西方世界採用的大多數理論體系的基礎。阿拉伯煉金術士在化學方面的功績,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通常估計。他們對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化學的歷史背景》)
精通科學史的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的結論是,正是因為阿拉伯帝國科學家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執著的科學精神,才使得現代化學得以產生
5、物理
阿拉伯帝國時期穆斯林在物理學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在於光學、力學(和動力學),以及對物質本質的認識。在力學方面,他們對物理學上的運動與慣性、時間與空間的概念的認識,和對拋物運動和重力作用的研究,為以後經典力學的建立做了必要的鋪墊。他們還有人認為在世界產生以前,原始狀態的物質是由具有空間範圍的、分散的“原子”構成的。在光學上阿拉伯帝國的物理學家提出了光線來自觀察的客體,認為光是以球面形式從光源發射出來的,進而認識光線的反射和折射現象。
偉大的物理學家金迪(al’Kindi,西元801?~873年,同時還是數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化學家和音樂理論家),一生至少著有265部以上的學術著作,但是傳世的只有15部拉丁文譯本。它們是關於氣象、比重、潮汐、(幾何)光學,以及音樂理論等方面的論述,許多內容是與物理有關的。
塔比特(Thabit ibn Qurrah,西元826~901年,兼數學家)是靜力學的奠基人,他寫了一部研究杠杆的力學著作——《杠杆的平衡》。他在該書中成功地證明了杠杆的平衡原理。
比魯尼(Biruni,西元973~1050年)研究過流體靜力學與物體的瞬間運動與加速度;他不僅發現光的傳播速度快於聲音,精確地測定了不同類型寶石的比重,並且為所有已知的複合物與物質元素建立了比重表,例如他測得金的比重為19.05~19.26,銅為8.72~8.83,水銀為12.74~13.59,與實際值相差不大,另外,還正確地解釋了噴泉與自流井的成因……
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稱為阿維森納Avicenna,西元980~1037年)不僅是醫學家,他還頗富獨創性地定義了諸如杠杆、滑輪和滾筒等機械裝置,並且把它們做了分類。傾角的概念也是伊本·西那提出的,藉以解釋物體的拋物運動,而這正是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的薄弱環節。
哈茲尼(al’Khazini)是繼塔比特研究杠杆平衡的最重要的科學家;他還設計一種奇妙的“智慧秤”,這種稱在沒有砝碼的情況下也能測量物質的重量和比重。為此他在1137年還寫了一本書——《智慧秤的故事》。哈茲尼對比重的研究卓有成效。他發現空氣具有重量,使得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在空氣中也能適用。哈茲尼還發現並證明越接近地心水的密度越大,而英國人羅傑·貝肯(Roger Bacon, 1214~1292年)則是在哈茲尼之後發現同一現象的。哈茲尼知道物體在不同高度測量的重量是不同的,進而提出了一種重要的物理學思想——物質的(質)量不同於重量,而且二者之間的關係是正比關係。
在光學研究中,哈森(al’Haitham或al’Haytham,西元965~1040年,歐洲人稱為Alhazen)為光線的物理學特性及幾何光學奠定了基礎,被稱作“光學之父”。他不僅說明光在同一物質中是沿直線傳播的,還研究了光的反射和折射,並且通過實驗指出,垂直穿透不同介質之間介面的光線是不彎曲的。他甚至擁有一台可以製作透鏡與研磨鏡片以供實驗使用的車床。他在實驗中不但研究平面鏡、球面鏡、柱面鏡和抛物面鏡,而且研究球面像差和透鏡的放大率,例如哈森發現透鏡的放大作用是由於光線穿過玻璃與空氣的交界面造成的,進而設想正是玻璃的弧度(透鏡曲率)導致放大作用的產生。大氣折射也是他研究的範疇。在光學研究中哈森善於應用數學方法解決幾何光學的問題。暗箱成像實驗也是哈森設計的,以此他正確解釋了暗箱的成像原理,因此約瑟夫•;黑爾甚至在《阿拉伯文明》一書中甚至將哈森評價為“照相攝影”的先驅。學習科學史的人或許瞭解著名的“哈森問題”,即在光源和眼睛位置固定的條件下,如何確定球面鏡、柱面鏡和圓錐面鏡上的反射點。例如對於球面鏡,哈森的答案是“平行於主軸的光線照射至球面鏡之後,都反射於主軸之上”。他關於球面像差、透鏡的放大率和大氣折射方面的發現通過開普勒等人的介紹,對歐洲科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哈森的一項重要貢獻是對視覺原理的闡釋。在哈森以前,人們一直堅信古希臘學者柏拉圖(Plato,西元前427~347年)和歐幾裡德(Euclid,約西元前3世紀)提出的“視覺是由於眼睛發射出光線照射於物體上而產生的”這一錯誤觀念,而哈森的觀點是——視覺是反射光線通過眼球的玻璃體後落在視網膜上才得到的,而圖像則最後產生於大腦。
哈森一生寫過大約92部著作,其中主要論題是關於光學、天文、幾何或數學。這位偉大的科學家的著作還被譯成拉丁語,啟發著後來的科學學家進一步探尋光學的奧秘。《哈森光學詞典》一書(或譯作《光學之書》,7卷),西元1270年被翻譯成拉丁語,譯名為Opticae thesauraus Alhazeni,是當時繼托勒密(Ptolemy,西元2世紀)之後光學領域最重要的科學成就,並且奠定了光學的基礎
6、實驗法
前文曾提及阿拉伯帝國科學家的實驗法,在此進一步加以闡述。
一位當時的學者伊本·泰米亞(ibn Taimiyya,西元1263~1327年)在《邏輯辯駁》一書中寫到:“歸納法是在可靠的論證過程中產生的,並最終導致了觀察和實驗法的產生。”
古代希臘人學習科學知識的途徑主要是通過思考、推測與推理。儘管希臘科學在當時取得過極其輝煌的成就,然而這種方法也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事實上,正是阿拉伯帝國的科學家們首先在科學研究中有條理地批駁以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希臘哲學思想,於是人類的科學研究活動開始生長出理論與實踐的兩隻翅膀,進入不同於希臘科學的一個時代。
有一位西方評論家寫到:“僅僅憑藉思考是不能發展科學的;科學的進步蘊藏在對自然研究的實踐之中。實驗與觀察是他們(阿拉伯人)研究方法的本質特點……在他們的著作裡,解決問題的方法總是通過做實驗與進行實驗觀察獲得的。”
哈森在《哈森光學詞典》中明確指出,他的發現就是源自在實驗中獲得的證據。換句話說,其光學研究是建立在科學實驗而非抽象的學說的基礎之上。事實上,這正是現代科學研究的方法,也是穆斯林與希臘前人的本質區別。哈森的實驗不僅系統性強且具有定量性,而且是可重複的。他總是設法獲得實驗資料之間的聯繫,或者說從實驗結果中歸納出學說和理論,並且把後者用數學形式加以表達。假如學說和理論適用於那些實驗資料,他就繼續進行進一步的實驗以期發現新的結果。
出於一種誤解或排斥,一些歐洲人極力否定阿拉伯帝國科學家在實驗法方面的地位,並且試圖把開創實驗法的榮耀與光環留給歐洲人自己。不抱偏見的科學史學家的研究表明,阿拉伯帝國的穆斯林早在1000多年前就建立了科學研究的實驗室從事科學實驗,並且將諸多科學發現加以公佈。
作者羅伯特·伯瑞弗爾特(Robert Briffault,1876~1948年)在《構建人性》中寫到:“牛津大學的繼承者羅傑·貝肯曾經學習阿拉伯語和阿拉伯科學,他不僅是穆斯林科學的信徒,而且將阿拉伯文和阿拉伯科學作為唯一的真知向他的同代人不厭其煩進行傳播和宣揚,並討論實驗法的淵源,澄清歐洲文明的源泉等。可以認為,阿拉伯人的實驗法就是由貝肯在他那個時代熱誠地在歐洲廣泛加以傳播的。”其實早期的西方大學,如牛津大學與巴黎大學都有阿拉伯系,羅傑·貝肯(Roger Bacon,西元1214~1292年)就一度是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的阿拉伯系研究學者或學生。他曾經長時期在西班牙的穆斯林科學之城托萊多留學與從事科學翻譯工作,並把許多科學著作帶回到英國。
從上段引文中人們不難看出,阿拉伯實驗科學通過這位生活在13世紀的歐洲人對後來的義大利人伽利略(Galileo,西元1564~1642年),或者還有英國人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西元1561~1627年)確定科學實驗的地位不無影響。事實是,後人所說的(法蘭西斯)培根哲學(Baconian Philosophy),或曰科學研究方法的三步驟——觀察、實驗和歸納,很早以前就被阿拉伯帝國的學者廣泛採用。
包括現代自然科學在內,科學無一不是建立在“觀察事實,用分析和實驗加以證實,進而建立科學的法則”的基礎上。因此實驗法在科學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實驗法,或稱其為實驗科學,是帝國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手段。借助實驗法,他們能夠在已知或完全未知的科學領域打開全新的視野,取得重大的突破。因此,這種建立在科學實驗基礎上的視野與突破,不僅本身就是科學編年史上黃金一樣的篇章,而且為現代自然科學的產生鋪墊了唯一的道路。
根據哈森的光學理論,穆斯林學者還成功地解釋了彩虹的成因,即彩虹是陽光在經過大氣水珠時發生折射和反射的結果。
阿拔斯·伊本·弗納斯(Abbas ibn Firnas,西元?~888年)是研究飛行動力學的先驅。西元875年,他憑藉自行設計、製造的“飛行器”在科爾多瓦城居民的目睹下嘗試“飛行”(滑翔)試驗,經過一段距離的滑翔之後,著陸時背部嚴重受傷,被譽為“飛行第一人”(西元852年摩爾人阿蒙·弗曼穿著翅膀樣斗篷從科爾多瓦的一座尖塔上縱身跳下嘗試“飛行”,落地時受輕傷)。這比義大利人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大約早了600年的時間。
其他還有Barlu Musa、al’Naziri、ibn Jami、al’Attar、Abdur Rahman ibn Nasr等人,都是從事過物理學研究的卓越的科學家;而且穆斯林還是鐘擺的發明者[鐘擺是天文學家尤努斯(也譯作尤尼,ibn Yunus,西元950?~1009年)發明的],庫特比(Kutbi)發明的鐘錶還曾被當時的哈裡發作為禮物贈與法蘭克國王查理曼(Charlemagne,西元742~814年)。
7、生物學
阿拉伯帝國生物學家對生物學的發展做出過傑出貢獻,帝國的學者、技術人員乃至勞動者專長于植物學、園藝、農業以及動物學知識或技術,尤其是西班牙的穆斯林把植物學、園藝、農業研究推向了巔峰狀態。
西班牙穆斯林植物學家採集大量植物標本加以系統性與科學性研究,並親自對栽培的植物進行分類。這或許是仰仗了伊比利亞半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他們還發現同種植物之間,如棕櫚和大麻各自存在性別差異。
迪納瓦利(al-Dinawari,西元?~895年)是穆斯林治理下西班牙的一位偉大的植物學家。他以6卷的篇幅(《植物之書》)記錄與描述了大量關於植物的論述,例如各種植物的特性與品質、生長過程與生長週期,以及植物對於土壤的不同要求。迪納瓦利研究的植物品種極其繁多,僅在其殘存的兩卷著作中,就涉及植物約400多種(包括農作物及水果),而且還將植物學與天文學和氣象學知識結合起來。
12世紀末出生於西班牙馬拉加的伊本·貝塔爾(ibn al’Baitar,?~1248年)堪稱那個時代最傑出的植物學家(兼藥物學家,見前文“醫藥學”部分)。其足跡遍佈西班牙、北非與小亞細亞等地中海地區。他記錄與描述的藥物達1400多條款,包括大量的藥用植物與蔬菜,並且著錄成書《醫方彙編》,其中首次介紹了此前不為人所知的200種新的植物。此書部分內容於1758年還在克雷默那被翻譯成拉丁語出版(見前文醫藥學部分)。
著名的植物學家伽菲奇(al’Ghafiqi,?~1165年),也對許多採集於西班牙和非洲的植物標本進行精確的記錄與描述,並且用阿拉伯語、拉丁語與柏柏爾語等不同語言命名植物。
其他還有Abdul Abbas al’Nabati、ibn Sauri、ibn Wahshiya、Zakariya al’Kaiwini、ibn Maskwaih等人,也都是那個時代傑出的植物學家。
穆斯林對植物學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今天,在西方的語言裡許多植物仍然沿用由阿拉伯語衍生的名稱,例如紅花、苜蓿等。
園藝也是穆斯林的至愛所在。植物學成就的取得,不僅促進了農業水準的提高,而且帶動了園藝學的進步,翠綠的植物園與修剪得體的花園遍佈巴格達、開羅、非斯(位於摩洛哥)和西班牙的科爾多瓦等地,歷史上的田園詩人曾經將它們比作人間的天堂。在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國部分地方,即當時曾經處於阿拉伯帝國統治或伊斯蘭文明影響的歐洲地區,即使今天人們仍然可以發現一些穆斯林園藝遺產或與之有關的文明古跡,例如格拉納達的愛爾罕布拉宮(別名“紅宮”)花園。而且以愛爾罕布拉宮花園為代表的西班牙園林,更成為歐洲園林的典範。《歷史上的花園》一文的作者威廉·霍珀也對這座花園給予熱情的肯定,而且在談及中世紀歐洲其它地方的鮮明反差時,霍珀則乾脆直言,其它地方簡直是滿目荒涼。
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年)說:“園藝學的改進構成了伊斯蘭最好的遺產。西班牙的園丁盛讚這是泥土最高貴的品德。園藝學的發展,使農業得到空前的繁榮,這也是西班牙穆斯林的榮耀之一。”
奧旺(ibn al’Awwam,12世紀)的《農業之書》是介紹農業與畜牧業的著作,可謂代表當時農業水準之集大成者。此書講述了585種植物和50種果樹的栽培與嫁接技術。他不僅講解了不同性質土壤的不同施肥的方法,而且講授了農業灌溉、作物雜交與多種植物疾病及其治療方法。
巴薩爾(ibn Bassal,11世紀)進行了土壤分類方面的研究,他把土壤劃分成10種類型,並且分析了土壤活力與季節變化的關係,以及不同土壤與作物對翻耕次數的不同要求。
在西班牙,穆斯林鋪設了縱橫交錯的灌溉網路,從而保證了農業的豐產豐收。在安達盧斯地區,他們創造的這種奇跡使得那裡被歷史學家稱作人間天堂。德弗紐克斯在他的著作——《黃金時代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寫到:“最值得稱頌的地方位於格拉納達一帶,摩爾人曾經長時期生活居住在這片自由的王國。他們通過水渠和隧道將水從白雪覆蓋的山巒引來澆灌平原及其周圍鮮花盛開的山坡,從而使得那裡成為具有世界上最美麗景色的地方之一。”的確,即使是今天的西班牙仍然受益于當年穆斯林修建的水利基礎,而西班牙語裡大量的諸如水渠、水池、灌溉稅等來自阿拉伯語水利方面的詞彙,則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穆斯林留下的歷史烙印。
具有重要意義的是,穆斯林把品種眾多的農作物帶到歐洲,它們包括甘蔗、棉花、茄子、柑橘、香蕉、海棗、洋薊、番紅花等,而穆斯林的歐洲鄰居們,從他們那裡學會了這些東西的稱謂,例如西班牙語的棉花一詞——algodon,就是來自阿拉伯語(al’qutn),英語的棉花——cotton,亦來源於此。雖然水稻最早據稱是羅馬人引入歐洲的,但是那時卻從未大規模種植,而是後來由穆斯林在建立了科學的灌溉系統的基礎上,大量引進與栽培的。穆斯林在歐洲推廣水稻的路線,首先是西班牙、西西里,然後是義大利的比薩平原與倫巴第地區。這些作物後來又被歐洲殖民者帶入美洲。
這些成果對於當時提高農業生產水準,解決人口的吃飯問題至關重要。鼎盛時期穆斯林治理下的西班牙面積占伊比利亞半島的大部或1/2強,在單位面積內養活的人口遠遠高於所有其它歐洲國家。創造這種奇跡沒有先進的農業技術的保障是根本不可能的,而這一切卻發生在西班牙,發生安達盧斯,發生在穆斯林治理西班牙的7~8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之中。
出生于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巴士拉城的賈希茲(al’Jahiz,西元776~869年)不僅是世界上第一個記錄鳥類遷徙的動物學家,他寫的一本介紹動物的書籍(《動物之書》),已經包含有動物心理學與社會行為的內容,尤其是還包含有進化論的萌芽。在動物的物種分類方面,他首先把動物以從簡單到複雜的鏈條穿起,並且根據它們之間的相似性劃分出不同的類別,然後再進一步劃分出亞類……如此分類下去直至終末。他發現環境因素對於動物生活的影響,以及動物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而發生的變化。
對於動物的“進化”機制,賈希茲提出了3個方面的學說,即,生存鬥爭、物種變化,及環境因素。
按照作者的觀點,這種生存鬥爭便是不同的個體彼此之間進行的“戰爭”,強者以弱者為食,弱者努力保護自我,這是造物主的法則。他還以鳥、大鼠、蛇、海狸、狐狸、鬣狗等為例來說明他的這種法則。例如,他說大鼠外出搜尋食物,捕食比它弱小的動物比如鳥,它同時需要隱蔽自己與幼子以躲避蛇的掠食。在賈希茲看來,這種鬥爭不僅在不同的物種之間存在,在相同的物種之間也是存在的。生存鬥爭其實就是一種自然的選擇,這是出於動物自我延續的天生的本能。
賈希茲認為,物種變化與變異是有可能發生的,環境因素也參與其中。他宣稱,原物種可以通過逐漸產生新的特徵而衍生出新形式的物種,這種新的特徵有助於其在所處的環境下生存。賈希茲在談及四足動物的時候說到:“有人能夠接受四足動物祖先的進化學說,並且認為狗、狼、狐狸以及與它們類似的動物都是由這種祖先產生的。”
至於環境因素,他提出食物、氣候、居所等要素對於物種具有生物學與心理學方面的影響。
賈希茲把物種變化的主要動力歸結為造物主的意志。
賈希茲是歷史上最早提出“進化論”的生物學家,他在動物學乃至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在後來穆斯林世界以及歐洲的生物學家身上產生不可磨滅的印記,例如瑞典的林內烏斯(Linnaeus,1707~1778年)、法國的布豐(Buffon,1707~1788年)與拉馬克(Lamarck,1744~1829年),以及英國的兩個達爾文(E. Darwin,1731~1802年;Charles R. Darwin,1809~1882年)。由此讀者不難發現,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的《物種起源》不是憑空產生的,換句話說,達爾文並非是從零開始的。
阿布·烏拜達(Abu Ubaidah,西元728~825年)對馬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他總共寫過100多部著作,其中有一半多是關於馬的。
埃及的達米利(al’Damiri,?~1405年)則是穆斯林世界最卓越的動物學家。他關於動物學的百科全書——《動物生活》,對動物發展史的介紹比布豐早了幾百年。
8、地理學
阿拉伯帝國時期的地理學內容極為豐富而詳實,既有繪圖學與海上探測的知識,也有旅行家對山川地貌的記錄,還包括測地學如對地理學座標甚為精確的數學測量與定量的地貌研究。學者的地理學知識不僅借鑒古巴比倫、印度、波斯與希臘的成果,而且建樹頗多,對之後航海時代的到來具有重要意義。他們繪製的地圖是繼希臘人之後對世界的最重要的認知,並具有質的進步,與中世紀歐洲基督教世界通行採用的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寰宇圖”則有天壤之別。
穆斯林的信仰要求人們開拓心智與視野,以及探究造物主造化的神奇,因此廣袤的土地無法羈絆他們走出去的腳步。旅行家與學者的長途旅行與考察是暢通的,即使是跨越帝國之中相互敵對的區域也是如此,而且大部分旅館依靠個人的捐款維持經營,並免費向旅行者開放。正如當時最傑出的地理學家比魯尼(Biruni,西元973~1050年)所言,伊斯蘭已經貫穿從東方到西方。
阿巴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是今天所謂的“科學的地理學”的發端時期,因為自那時以來地理學便真正成為“定量加描述性地理學”。穆斯林學者不僅從印度天文學書籍裡學習很多長度計算方法,而且還從希臘與波斯的著作中受益非淺,進而建立“定量加描述性地理學”。
地理學家在大地測量學方面頗有建樹,如測定城市的方位、山峰的高度等,甚至在測量地球的半(直)徑、周長、經度等方面,也做過有益而富有成果的嘗試(假定地球為圓形)。
比魯尼,堪稱定量加描述性地理學即科學地理學的先驅,其代表作是原本用來確定穆斯林禮拜朝向的《城市方位座標的確定》。這部著作以及比魯尼其它地理學著作的特點是,在地理學上追求數學的精確與論證的嚴謹,這與他深厚的數學及天文學功底是分不開的。事實上比魯尼同時是以偉大的數學家與天文學家聞名的。他對地理學的貢獻主要在於,他發明了採用三角測量法測量大地及地面物體之間的距離的技術,並測量了地球半徑,換算成今天通行的長度單位為6339.6千米,這與現在我們所掌握數值(赤道半徑6378.140千米,極半徑6356.755千米,平均半徑6371.004千米)已經相差無幾。他的貢獻還在於對地球的經、緯度做出精密的測量,改進了經、緯度的測定方法,並且發明了測量山峰和其它物體高度的方法。比魯尼總共撰寫了15部大地測量學(或數學地理學)著作,《繪圖法》是其青年時代的作品;《古代國家編年史》講述的是古代各民族的歷史和紀元,涉及很多地理知識,蒙莉莎媒體出版社甚至在1984年還發行出版過此書;《印度》介紹了關於印度的自然與社會知識,包括提供了那裡豐富的地理學資訊。
比魯尼可謂是中世紀地理學第一巨人,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年)則乾脆把11世紀(上半葉)命名為“比魯尼的世紀”。
此外,歷史上一幅著名的世界地圖——“馬蒙地圖”誕生於西元9世紀初阿巴斯王朝的哈裡發馬蒙時期(西元813~833年)。
有一部集宇宙天體、歷史與地理於一體的百科全書——《黃金草原》,其作者馬蘇德(al’Masudi,西元895?~957年)是一位生活在(9~)10世紀的著名阿拉伯旅行家,在西亞、南亞、南歐和東非都遍佈他旅行考察的足跡。《黃金草原》在以後數百年間被從事自然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在學術著作中廣泛引用。
伊斯蘭教要求,在經濟與身體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一個穆斯林一生之中至少需要赴麥加朝覲一次,此外,穆斯林素有外出經商的傳統,他們熱愛旅行和探險,這些都對地理學的發展提出很高的要求並且起到了促進的作用。當時的地理學家利用他們掌握的天文學與數學知識,繪製出各種地圖,出版了許多旅遊書籍。
穆卡達西(Al’Muqaddasi,西元945年~?)是第一個使用自然色彩繪製地圖的地理學家,他大約在西元985年完成並發表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學著作——《地域知識》。當代學者給予穆卡達西極高的評價,克雷默斯稱:“那些在現代地理學中令人感興趣的科目,沒有穆卡達西未涉足的。”米克爾則稱其為“所有地理學科的開創者”。雅庫比(al’Ya’qubi)在進行了長時間旅行考察的基礎上,於西元891年完成《國家》一書。該書詳細介紹了各地區城鎮與國家的名稱、城鎮之間的距離、地形地貌、水資源,以及百姓、統治者和稅賦的情況。伊本·克達比(ibn Khurdadhbih,西元?~912年)是《交通與行省》的作者。此書繪製了穆斯林世界所有貿易線路的地圖並給出了文字說明,介紹的貿易線路甚至遠達東亞的中國、朝鮮和日本、南亞的雅魯藏布江、安達曼群島、馬來亞與爪哇。曾經在西班牙的科爾多瓦工作過的地理學家易德里斯(al’Idrisi,拉丁名Dreses,1099或1100~1166年)來自穆斯林世界,但後來就職于諾曼第人羅傑二世(Roger Ⅱ)的西西里宮廷。他編撰過以贊助人羅傑二世命名的《羅傑之書》(也稱《世界地理》),並且繪製了一幅圓形地圖——世界地圖,以及製作了一架銀質的天球儀,可謂那個時代的奇跡。內有70張地圖的《直通天空台》一書也是他的作品。雅古巴·哈馬維(Yagubal Hamawi,1179~1229年)則寫作了內容翔實的《地理詞典》。
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1304~1369年)是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他在21歲的時候就離開家鄉坦吉爾,從此開始了長達近30年的旅行。伊本·白圖泰也許是在蒸汽機車產生之前合計旅行距離最長的旅行家。除了訪問過西亞、北非和西班牙等所有伊斯蘭國家和地區之外,他的旅行足跡還遠至亞撒哈拉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和東部非洲,南亞的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代夫,以及歐洲的拜占廷、南俄和中國等地。在中國的杭州、泉州(刺桐港)以及北京(元大都)等地都留下這位偉大的旅行家旅行、考察的足跡。
伊本·白圖泰結束旅行返回摩洛哥之後,口述其旅行見聞,經過伊本·祖紮伊·卡爾比(ibn Juzay al’Kalbi)三個月的記錄與整理,而成《伊本·白圖泰遊記》。這部旅行家筆錄,以豐富翔實的資料,成為介紹中世紀地理、歷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價值極高的著作,長期被許多學者研究、引用。
指南針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把指南針加工成羅盤用於航海則是穆斯林的創造,這也為海上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技術基礎。
從西元10~11世紀開始,伴隨海上貿易的發展,海洋地理學揭開了新篇章。穆斯林航海家、水手、商人與傳教者揚帆遠航,足跡遍佈四海重洋。除了去往歐洲之外,他們越過今天的印度洋,進入太平洋,抵達南洋群島的爪哇、蘇門答臘、呂宋,最後來到中國,甚至可能先於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46?~1506年)500年從西班牙及西非到達美洲。穆斯林們在與大海為伍的同時,積累了豐富的海洋地理學知識。他們熟悉航行的各個不同的海域,認識颱風的威力,掌握季風的規律。這些與地理學有關的知識隨著他們的足跡傳播到東、西方,為後來的航海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例如氣象學術語“typhoon”(颱風)一詞,便是來源於阿拉伯語音譯“tufan”,“monsoon”(季風)一詞則是源自“mawsim”。
三、文獻翻譯
阿拉伯帝國在推進疆界的同時,繼承了大量先人的科學文獻。帝國不但很好地保存這些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而且還著手進行意義重大的文獻翻譯工作,包括翻譯幾乎全部的希臘著作。
在倭馬亞王朝(中國史書稱為“白衣大食”,西元661~750年)時期,就有部分翻譯家自發地翻譯用古敘利亞語——阿拉馬語書寫的醫學與天文學著作。但是,這一時期的翻譯活動一般還不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規劃和組織下進行的。
自西元750年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建立後,隨著對外征服活動的減少,社會趨向于安定,經濟進一步發展,科學文化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文獻翻譯活動也得以大規模進行。歷史學家通常將這一時期稱作伊斯蘭及伊斯蘭科學的“黃金時期”,其中以哈裡發馬蒙時期(西元813~833年)的翻譯工作尤為突出,都城巴格達於是也成為舉世聞名的科學翻譯中心。歷史上著名的“智慧宮”就開始興盛于哈裡發馬蒙時期。“智慧宮”是一所集圖書館、科學院和翻譯局于一體的綜合性圖書館及科學研究機構。在政府的主持下,當時一流的專家、學者聚集于此,把包括科學圖書在內的大量古埃及、希臘、羅馬、波斯和印度的古籍翻譯成阿拉伯語。馬蒙熱心於贊助科學文獻的翻譯工作,據說他曾以與譯稿等重的黃金酬謝著名翻譯家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西元809~873年,歐洲人稱之為Joannitius,兼翻譯家與數學家,基督徒)。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曾經遊歷於希臘語國家收集資料與手稿,並將大量有價值的文獻翻譯、整理及保存下來。
阿拉伯帝國的學者並沒有滿足于通過翻譯所獲得的知識,或者說他們的工作絕非簡單的翻譯與被動的接收,而是校正了很多的古籍的錯誤與不足,並進行深入的考證與細緻的詮釋和評價,進而創立自己的科學理論。這可謂是帝國科學的顯著特點之一。
阿拉伯帝國的翻譯家的辛勤勞動也為人類留下了珍貴的遺產,這些遺產後來又通過帝國版圖上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國部分地區傳遍歐洲,成為點燃文藝復興的文明的火種。
四、阿拉伯帝國與中華文明的交流
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科學與文化交流在帝國建立之前的很長時間就已經存在了。以伊斯蘭文明為特徵的阿拉伯帝國興起後,恰逢中國歷史上科學技術發達的大唐王朝與兩宋,因此兩種文明的交流與借鑒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況且帝國的穆斯林向來有四海為家的傳統。
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曾經告戒他的弟子說:“知識即使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據《舊唐書·西域傳》記載,唐高宗永徽二年(西元651年),大食國(阿拉伯帝國)第三任正統哈裡發奧斯曼(Uthman ibn Affan,西元?~656年)派遣使節抵達長安與唐朝通好,唐高宗即為穆斯林使節赦建清真寺。此後雙方來往頻繁,見於我國史書記載的,大食使節來華次數至少達37次之多。安史之亂暴發後,西元757年唐朝向大食求援,大食即派遣軍兵幫助平定安史之亂,這些人後來也大多留在了中國成為中國回回人的先人之一。
西元8世紀中葉,中國的杜環(在怛邏斯戰役中被俘)去過阿拉伯地區,足跡遠至北非馬格裡布地區的摩洛哥等地,並且將其所見所聞寫成一本書——《經行記》,不僅為中國人瞭解阿拉伯帝國及穆斯林世界打開了一扇視窗,也為中、阿文明交往留下珍貴的資料。可惜杜環的《經行記》原書失傳,但是其族叔杜佑在所著《通典》中摘引數段;此外《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通志》和《文獻通考》亦有少量轉引。
中國的“四大發明”最早傳出的是造紙術。西元8世紀,也就是在大食第三任正統哈裡發奧斯曼派遣使節來大唐的大約100年之後,外部世界的第一個造紙作坊就出現在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旅程和王國》一書有這樣一句話——“紙是由俘虜自中國引入撒馬爾罕的。”這裡所說的俘虜即指在怛邏斯戰役中被俘的一些中國造紙工匠。在時間上前後幾乎相差無幾,巴格達也出現了造紙作坊,之後逐漸擴展到大馬士革、開羅,以及摩洛哥與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達也好,撒馬爾罕也好,造紙技術全部都是由來自中國的造紙工匠傳授的,而且這種技術後來又被傳往歐洲。中國的造紙工匠除了在怛邏斯戰役中被俘後流落它鄉傳播造紙技術,也可能是作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邏斯戰役之前就到達了那裡,或者兼而有之。另外,在西元8世紀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西元750~1258年,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的大城市裡,已經出現來自中國的綾絹機杼,並且還有來自中國的技師(金銀匠、畫匠及紡織技術人員等)在當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劉泚為“漢匠起作畫者”,河東人樂×、呂禮為“織絡者”[(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繼造紙術之後,一些中國的其它發明創造也通過著名的絲綢之路傳進阿拉伯帝國,後來通過帝國版圖上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國部分地區傳遍歐洲,對西方的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文明的交流是互相的,伴隨科學與文化交流的發展,不僅伊斯蘭教傳入了中國,而且阿拉伯帝國先進的數學、天文曆算、醫藥以及航海、地理知識為中國人所瞭解。例如,他們先進的醫藥學知識大大豐富了中醫藥學的內涵,我們今天所能使用的中藥,相當一部分就是當年穆斯林商人與醫藥學家從阿拉伯、波斯與印度等地引進的“海藥”(唐代官員已經開始用文字記載這些影響)。而且帝國來華的穆斯林自唐代以來,已有人開始長期在長安、廣州、泉州、杭州、南京、揚州及北京(大都)等重要城市居住,直接參與中華文明發展的進程。正是由於受到這種外來文明的影響,中國人便開始認識、學習伊斯蘭科學,例如13世紀元代的穆斯林天文學家劄馬魯丁引進、設計、製造的世界上罕有的地球儀等7種天文儀器,進而明代的鄭和船隊在15世紀甚至開創了七下西洋的壯舉……
伊本·納迪姆(ibn al’Nadim,西元?~999年)在《科學書目》中,還記錄了阿拉伯帝國著名醫學家拉齊(al’Razi,歐洲人稱其為Rhazes,西元865~925?年)幫助一位中國醫藥學家的故事。這位在巴格達學習並且住在拉齊家裡的中國醫藥學家,在回國之前請求拉齊為他讀蓋倫醫學著作的16卷阿拉伯文譯本。拉齊滿足了他的要求,他則以中國的“速寫法”(草書)記錄全文並將之帶回中國。20世紀英國的科學史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也採納了這個故事。
海上絲綢之路大約興起於西元9世紀初,這也是維繫兩種文明交流的紐帶。西元10世紀,阿拉伯商人蘇萊曼與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與西拉夫(古代波斯灣港口)經海路駛進中國的廣州港。之後,他們對於中國風土人情的大量的敘述(由阿布·賽義德·哈桑整理出版),使得當時的阿拉伯世界進一步認識了中國。此類故事或許也為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提供了與中國有關的素材。
中華文明與阿拉伯文明融會貫通、互通有無、彼此借鑒,共同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這種文明的交往堪稱人類一切文明交往的典範。
五、關於焚燒亞歷山大圖書館的謊言
現在讓我們來戳穿一個關於穆斯林征服者焚毀亞力山大圖書館的謊言,以便使“瘋狂焚燒托勒密書稿”這樣的寓言故事就此止步。
西元642年,阿拉伯軍隊在阿莫爾·本·阿綏的統帥下進入埃及的亞力山大城,一種傳說認為阿莫爾奉哈裡發歐麥爾(Umar,西元634~644年在位)之命將亞力山大圖書館放火焚毀。據傳歐麥爾的理由是,如果這些希臘人的著作與安拉的經典一致,它們就沒有保存的必要了,因為現有的經典已經足夠了;倘若它們不一致,則是有害的,應該被摧毀。總之,毀滅它們是合理的。
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說:“所謂的焚燒亞力山大圖書館這樣荒蠻的行為並不符合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道德準則。人們會產生這樣的質疑——那些傑出的學者們長久以來怎麼會相信這樣一種傳說?這種傳說遭到我們這個時代唾棄,根本沒有再去討論必要了。沒有什麼事情比證明在伊斯蘭征服世界以前,是基督徒自己焚毀了異教徒的書籍更容易了。”
奇怪的是,那些穆斯林征服時代或稍晚一些的、人才濟濟的歷史學家(包括埃及的基督徒歷史學家例如Eustichius與Elmacin),一概保持緘默,沒有一人留下對焚燒亞力山大圖書館事件的片言隻語的記載,倒是過了大約500多年到13世紀突然冒出三個人講起這個故事,其中尤以一個叫伊勃努爾·希伯萊(Ibnul al’Ibri,意思是“猶太人的兒子”)的人的說法經不起推敲。
按照這位“猶太人的兒子”的說法,那些被焚燒的70萬冊圖書被亞力山大的4000座浴室當作燃料連續燃燒了半年的時間。但是,這種說法卻出現了簡單的算數問題——如果把按此人所說的70萬冊圖書分送到4000座浴室,那麼每個浴室只能分到175本,而要想讓這175本書連續焚燒半年,則每本書至少需要持續燃燒一天以上。所以,人們有理由提出這樣的疑問——什麼樣的書可以連續燃燒24個小時?況且多達70萬冊這一數量本身就是令人無法相信的。由此聽眾完全可以否定這個“猶太人的兒子”講述的“寓言”的真實性了。
事實上在阿拉伯軍隊進入埃及以前,亞力山大圖書館幾經破壞,並且至少被放了兩次大火,一次在西元前47年,放火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利斯·愷撒(Julius Caesar,西元前101~44年)的艦隊,另一次在西元391年,適值羅馬帝國分裂前的最後一位暴君——狄奧多西(Theodosius,西元347~395年)統治時期,而等到西元7世紀阿拉伯人進入亞力山大城的時候,這座圖書館已經名不見經傳,沒有什麼地位可言了。許多歷史資料都提到這兩次大火。莫非“猶太人的兒子”以那兩次大火為藍本,杜撰了一個新的寓言故事?
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在《阿拉伯通史》中也對這個故事持否定態度。他說:“巴格達人阿卜杜勒·萊兌弗(回曆629年,即西元1231年卒)似乎是首先敘述這個故事的人。他杜撰這個故事的目的何在,不得而知;但是,後來的著作家,以訛傳訛,把這種說法大肆渲染,好像實有其事一樣。”
“每一個基督徒都被灌輸以這個故事——哈裡發摧毀了亞力山大圖書館。”貝特朗·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的一席話直接點明了西方人熱衷於排斥“異教徒”的要害。他寫到:“與不僅迫害異教徒,而且自相殘殺的基督徒形成對照的是,穆斯林因寬宏而受到歡迎,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他們的征服活動。在後來的一些時候,對猶太人和摩爾人的狂熱的憎恨毀壞了西班牙,法國也因對胡格諾教徒的迫害受到悲慘的削弱。”可見,在羅素看來,中世紀的西方人自己倒是蠻適合扮演放火者這一角色的。西班牙的費迪南(Ferdinand II,1452~1516年)和伊莎貝拉(Isabella I,1451-1504年)兩位陛下,不就以把穆斯林與猶太人的書稿投進烈焰為榮耀嗎?英國作家科林·威爾遜曾就西元391年亞力山大城主教在狄奧多西支持下,下令焚燒圖書館加以諷刺——知識是邪惡的,亞當就曾因為求知而被逐出伊甸園。有位教皇也有一句名言——無知乃虔誠之母。
當代一些人對於傳播此類“燒館”的故事樂此不疲,可能緣於盲信,但也不排除出於有意的動機。約瑟夫·巴納巴斯甚至將“燒館”的行為比做納粹,有一位叫喬格的印度人則更加直白地表露說,穆斯林的所做所為完全是出自他們的宗教。看來有的作者似乎並不在意“燒館”事件的荒謬與否,獲得“穆斯林是科學的敵人”這種結論,才是他們的筆鋒所向
六、地位與學者評價
當歐洲籠罩於基督教的黑暗之時,以伊斯蘭為特徵的阿拉伯帝國的文明光芒璀璨,成就斐然。對於這種文明的地位,權威的科學史學家的評價是,縱向來看,它在人類歷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臘、羅馬)啟後(文藝復興)的作用;橫向來看,東、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威爾斯(H.G. Wells,1866~1946年)寫到:“由希臘人開創的對資料的系統性的積累,因傘族人(閃米特人,此處指阿拉伯人——筆者注)令人震驚的復興而得以繼續。亞里斯多德和亞歷山大博物館的種子久已沉睡,失去生機且被遺忘,如今開始開花結果了。”(《世界簡史》)
而居斯塔夫·勒朋(Gustav Lebon,1841~1931年)則寫道:“阿拉伯人迅速地創立了一種與以往的許多文化有著很大差異的新興文明。由於他們良好的政策,使許多民族接受了他們的宗教、語言和文化,連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們情願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傳統習慣和建築藝術……”
瞭解一些科學史的人都知道,歷史上西方學者曾廣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於阿拉伯帝國的科學文化,許多科學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語撰寫的,帝國在此期間也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學家。因此,前西德歷史學家赫伯特·格特沙爾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蘭教》一書中寫到:“全世界都感謝阿拉伯語在傳播中世紀高度發展的阿拉伯科學知識方面所帶來的媒體作用……如果沒有阿拉伯語這個媒介,得到這些知識是不可想像的,或者說無論如何也不會瞭解得那麼早。”
歷史學家希提(Phillip Hitti,1886~1978年)的《阿拉伯通史》有這樣一段話:“如果我們把那些以阿拉伯語為母語的人視為阿拉伯人,而且地域不僅僅局限於阿拉伯半島,那麼在中世紀的第一個篇章裡,就人類進步而言,沒有任何民族做出的貢獻堪與他們相比。除了遠東之外,數個世紀以來阿拉伯語在整個文明世界作為學術、文化和知識進步的語言。”
作者羅伯特·伯瑞弗爾特(Robert Briffault,1876~1948年)在《構建人性》中則更加明確地說:“如果沒有阿拉伯人,現代的歐洲文明就根本不會出現,這是極其可能的;絕對可以肯定,如果沒有他們,歐洲便不會扮演那麼一種超越所有先前進步階段的角色。”“正是在阿拉伯與摩爾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藝復興才得以發生。正是西班牙而非義大利,成為歐洲再生的搖籃……”
居斯塔夫·勒朋還旗幟鮮明地指出:“十字軍戰爭不是導致學術進入歐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過西班牙、西西里和義大利。”
《西班牙的摩爾人》的作者、英國人斯坦利·萊恩普爾(Stanley Lane-Poole,1854~1931年)說:“西班牙在穆斯林統治下的近8個世紀裡,發展成為整個歐洲文明的光輝典範——當歐洲其它地方呈現蕭條的時候,這個國度的藝術、文學與科學一片繁榮。來自法國、德國與英國的求學者聚集在這裡,汲取這些流淌在摩爾人的城市裡的知識的甘泉。”歷史上,在西班牙科爾多瓦、塞維利亞與格拉納達的高等學府裡,雲集著為數眾多的基督徒與猶太學生,他們如饑似渴地向穆斯林學者學習科學,然後又把所學到的知識在歐洲播散。
以下引用當時英國國王喬治二世寫給西班牙哈裡發希沙姆三世(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請求哈裡發允許他派遣王族成員前往科爾多瓦大學學習。
“喬治二世——英國、高盧、瑞典及挪威的國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國王哈裡發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們已經獲悉,貴國之科學、知識、技術與製造業甚為發達,故,鑒於我們的國家在此類方面之匱乏,及全然處於愚昧無知,我們希望獲得良機,以使我們的青年人受益於貴方之成就。
我們期盼這種良機可以讓我們跟隨你們的腳步前進,並以知識照亮我們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國貴族女子,希望受惠於你們的學術機構(科爾多瓦大學——筆者注)。對您特許給予我們機會以實現我們的目標致以敬意。
年輕的公主將為陛下晉獻一份禮物。您若能夠收下我們將倍感榮幸。
落款:您順從的僕人——喬治”
西班牙穆斯林創建的大學也是後來一些歐洲早期的大學的模範,例如阿方索八世於西元1208年建立的帕倫西亞大學與弗雷德里克二世於西元1224年建立的那不勒斯大學。
儘管基督教世界翻譯穆斯林的科學著作在諸如巴塞羅納、里昂或圖盧茲等地都有進行,但是佔據首要位置的無疑是西班牙的托萊多。這座從西元8世紀至11世紀下半葉的3~4百年之間由阿拉伯或摩爾穆斯林治理的城市,開始成為整個歐洲的文化聚集之地,其聲望尤其是在翻譯工作大規模開展的12世紀以來,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在托萊多被譯成拉丁語的穆斯林科學著作,至少應該有幾百部以上或者更多。事實上,歐洲也因此而湧現出諸如桑塔拉的休(Hugh of Santalla,1119~1151年)、克雷莫納的傑拉德(Gerard of Cremona,1114~1187年)、普拉托(Plato)、阿德拉爾德(Adelard,1075~1160年)、羅傑·貝肯(Roger Bacon,1214~1292年),以及賈斯特的羅伯特(Robert of Chester,成名於西元1145年)和荷爾曼等著名的翻譯家。這些翻譯家來自歐洲各地,他們雲集於此,如饑似渴地從事科學著作的翻譯工作[在那些翻譯家來到托萊多之前不久,那裡甚至還出現了後來成為羅馬教皇的吉伯特(Gerbertd Aurillac,西元945~1003年,即西爾維斯特二世——Sylvester II,任職999~1003年)的身影]。《全球通史》也提到這些翻譯家,它寫到:“12、13世紀,這裡的翻譯家有猶太人、西班牙人和歐洲各地的外國學者。”可以這樣說,他們來到托萊多的目的只有一個——盡一切可能獲取穆斯林的科學知識。
事實上,自西元12世紀阿拉伯帝國學者的著作(和希臘、羅馬著作的阿拉伯語譯本)被大批譯成拉丁語及其它歐洲語言以來,歐洲各大學將它們作為教科書長達幾個世紀。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講,所謂的歐洲的“復興”,又何嘗不是穆斯林科學的傳承。
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阿拉伯帝國的科學技術與文化承前啟後,獨步中古。如果將《構建人性》加以引申,人們就會明確無誤地看到,彼時其科學技術與文化水準代表當時人類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國的文明在科學上多有建樹,而且正是通過廣大科學家與學者的創造性勞動,古代印度、希臘、波斯的科學巨著得以矯正並保存。
歐洲文藝復興的大師們從阿拉伯語書寫的科學巨著開始,點燃了復興的火炬。如果沒有崇尚科學的穆斯林的辛勤勞動,今天就不會有人看到歐幾裡德的《幾何原本》了;因為中世紀籠罩在歐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幾乎摧毀了一切古代希臘的科學文化典籍,儘管衰敗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隻語。不要輕視阿拉伯帝國科學的作用——當苟延殘喘的拜占廷帝國幾乎完全隔絕歐洲通向東方的道路之時,中國的“四大發明”是經由當時在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影響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國部分地區,傳往整個義大利乃至歐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學基礎的文藝復興,正是始於歐洲的這些地方。
對此,《伊斯蘭的遺產》有所佐證。該書寫到:“回顧歷史,我們可以這樣講,伊斯蘭(醫學與)科學映射著希臘的光芒,當希臘科學的白晝流逝,伊斯蘭(醫學與)科學的光輝猶如月亮,照耀著中世紀歐洲最黑暗的夜晚……因為伊斯蘭(醫學與)科學指引或引導了那場偉大的運動(文藝復興),所以我們有理由宣稱這種文明依然與我們同在。”
流傳下來的阿拉伯帝國科學的歷史文稿有時是很粗略的,這使得一些人產生這樣一種錯覺,即它的科學只不過是對希臘科學在歐洲科學革命之前的一種保存。出現這種錯覺的原因恐怕還在於,中世紀阿拉伯帝國的科學著作幾乎都是以阿拉伯語書寫的,今天的科學編年史學家真正精通這種科學語言的已經不多了,況且既精通語言又接受過科學訓練的歷史學家則更如鳳毛麟角。另外,一些被翻譯成拉丁語或其它語言的阿拉伯帝國的科學書籍,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有所變化和改動,讀者已然很難分辨它們的淵源了。還有一個原因可能在於,一些人有意或無意地進行了“模糊”處理。
但是,更有一些史學家力圖歪曲史實,公然宣稱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只不過是希臘、羅馬文化的一點餘光。”其實,這種蓄意抹殺阿拉伯帝國的科學地位與成就的鼓噪,不是出於無知,就是緣於偏見,並且以後一種可能性最大。而事實是足以勝過詭辯的。
諸如奧托·紐格堡(Otto Neugebauer,1899~1990年,奧地利)與德拉姆伯瑞(Delambre,1749~1822年,法國)之類所謂的學者甚至走的更遠。例如在他們的報告裡,伊斯蘭天文學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過,儘管那時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樣俯瞰著大地,然而穆斯林好像從來不曾凝視過星空。而皮埃爾·杜希姆(Pierre Duhem,1861~1916年,法國)的態度則可謂是滑稽可笑了。按著他的邏輯,中世紀的穆斯林在天文學方面同時身兼兩重身份——一是瘋狂焚燒托勒密(Ptolemy,西元2世紀)書稿的暴徒,二是毫無建樹地模仿希臘科學的抄寫員。可是,一個抄寫員如何能夠眷抄一部已經投進烈焰的書稿?這就好比讓皮埃爾·杜希姆先生用自己的腳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樣困難。前文對穆斯林焚毀亞力山大圖書館謊言的戳穿,已足以令皮埃爾·杜希姆之類的“偽術士”在天真的讀者面前被徹底揭去偽裝的面皮。
此類荒唐的邏輯也不乏追隨者,他們甚至企圖使人類的天文學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這一步蛙跳幾乎有1500年的距離。先後擔任國英國歐文學院與曼徹斯特大學歷史系教授的湯瑪斯·陶特(Thomas Frederick Tout,1855~1929年)說:“看到還有人相信,一個人能夠從伯裡克利或奧古斯都時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十四時代,這實在令人痛心……從頭開始固然好,但是我們根本不能隨意在某個時候停下來,跳躍過數百年,然後重新開始。”
約翰·威廉·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11~1882年)在《歐洲知識發展史》一書中仗義執言說到:“歐洲文獻故意系統性地抹殺穆斯林的科學成就,對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憤。但是我肯定,他們再也不會繼續被隱瞞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敵視與民族自負基礎上的偏見永遠都不會長久。”
貝特朗·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也在《西方哲學史》中批駁說:“對於我們來說,似乎只有西歐文明才是文明,這是狹隘的偏見。”
在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1884~1956年)的《科學史導引》中有這樣一段話——“有一些榮耀的名字足以讓人們想起,在西方是沒有同時代的人物能夠與這些名字相匹敵的……加長由這些名字組成的豪華的名單也並不是困難的。如果有人告訴你說中世紀的科學沒有什麼進步,那麼就把這些名字讀給他聽,他們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長的時期內——西元750~1100年,取得輝煌成就的。”
讓我們回味一下喬治·薩頓的一句話的含義吧——“一個自以為是和虛偽的哲學家不可能理解伊斯蘭的智慧,同樣也應受到譴責。”
希提寫到:“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區、波斯和埃及的國土後,阿拉伯人不僅佔有一些地理上的地區,而且佔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發祥地。沙漠的居民成為那些古老文化的繼承者,淵源於希臘-羅馬時代、波斯時代、法老時代和亞述-巴比倫時代的那些歷史悠久的傳統,也由他們繼承下來……這些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在他們所管轄的人民的合作和幫助之下,開始消化、採用和複製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學遺產……他們是征服者成為被征服者的俘虜的另一個例證。”作為人類文化遺產鏈條的重要一環,可見阿拉伯帝國的文明在包容性與多元性上堪稱典範。他進一步寫到:“在整個哈裡發政府時代,敘利亞人,波斯人、埃及人等,作為新入教的穆斯林,或作為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他們自始至終舉著教學和科研的火炬,走在最前列……從另一種意義來說,這種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區古代閃族文化邏輯的繼續……”
約翰·威廉·德雷珀還對伊斯蘭科學的寬容加以讚揚,他指出:“在哈裡發時期,學識淵博的基督徒與猶太教徒不僅受到應有的尊敬,而且被委以重任,提拔在政府中擔任高級職務。”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智慧宮”中的著名翻譯家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西元809~873年,歐洲人稱之為Joannitius,兼翻譯家與數學家)就是一名基督徒。這種做法與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宗教裁判所瘋狂毀滅科學,殘酷迫害追求知識的學者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前文引用的文獻作者皆為研究歷史或科學史的著名學者。另外,也有一些“大眾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但願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學無術、胡說八道。
《自然辯證法》一書指出:“古代留傳下歐幾裡德幾何學和托勒密大陽系;阿拉伯留傳下十進位制、代數學的發端、現代數字和煉金術;基督教的中世紀什麼也沒有留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對科學史的評價。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抓住時機》中說:“當歐洲還處於中世紀的蒙昧狀態的時候,伊斯蘭文明正經歷著它的黃金時代……幾乎所有領域的關鍵性進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人們把知識的邊界往前開拓的時候,他們所以能眼光看到更遠,是因為他們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七、結束語
世界上各種開放的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互相學習、互相吸收、互相補充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現象,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規律。
阿拉伯帝國的科學成就,其實是包括阿拉伯人在內的穆斯林共同體(還應包括帝國境內的非穆斯林),在吸收其它先進文化基礎上的智慧的結晶。所謂的阿拉伯科學的主體,並非僅指阿拉伯人,甚至可以說當時多半著名的科學家與學者是非阿拉伯裔的。但是,他們以同一種的語言——阿拉伯語,書寫科學著作。除了自身的探索之外,許多希臘、羅馬、波斯、印度甚至中國的科學典籍都是他們靈感的源泉。這些人類的文化積澱不但在他們手裡被賦予一種全新的理解,而且他們自身也頗有創新,獨樹一幟。他們求知不倦,是“知識即使遠在中國亦當往求之”的踐行者。他們不僅是阿拉伯等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民族的驕傲,而且其成就也是全人類的文化瑰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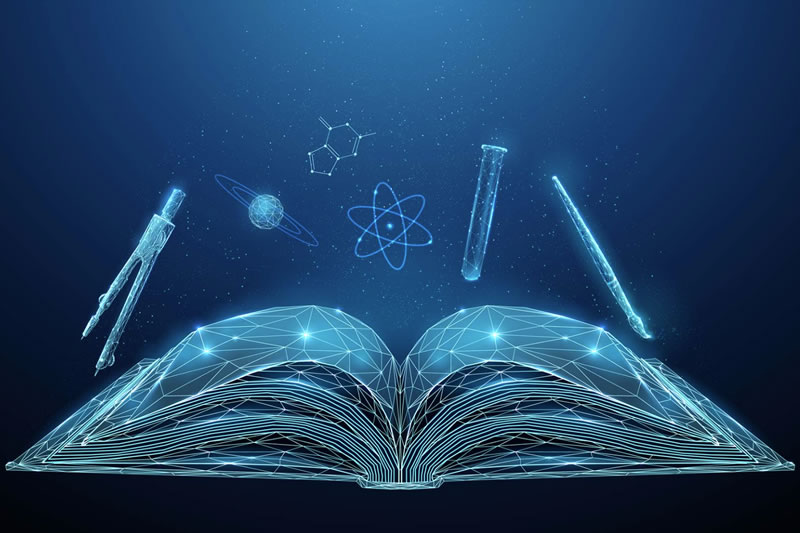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