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曾寫過同樣題目的一篇文章,存到閃盤中。後來閃盤毀壞,文字也隨之消於無形。以後又曾在許多場合講過這個題目,但直到現在才有了將它重新形成文字的機會。
雖然自己比較喜歡以邏輯思辨的方式來歸納與梳理伊斯蘭信仰方面的義理,但面對這個題目,卻很難“心平氣和”地進行所謂“冷靜而客觀”的論述,因為每每此時,它總會讓我的心底湧起一股無以言表的熱流,仿佛體內那些乾癟的生命細胞突然被一下子注滿了新鮮的血液,頓時膨脹與活躍起來。
一個真正的信仰者在其一生中都要和宇宙的造物主“相遇”,只要我們走向他,他就會迎向我們。這可能就是對一般穆斯林所稱之為“定信”體驗的真實寫照。由於生活中的一些特殊考驗與經遇,我與宇宙的造物主——安拉之間好像不僅僅是一個“相遇”的過程,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講還是一個“相知”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就是自己在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生平傳記中的多次穿行與遊歷,直到找尋到那些能夠讓自己對來自安拉考驗的抱怨感到羞赧的那些先知的生活點滴。
我曾不止一次向別人談到,是聖傳醫治了我脆弱而殘傷的心靈。
記得十多年前在閱讀一本伊斯蘭的著作時,該書作者將先知穆罕默德的人格準確地定位為“宇宙人格”。當時那種醍醐灌頂的感覺至今仍歷歷在目——“宇宙人格”!除了這種定位外,還能有更為精准而恰切、透徹而本質地揭示先知精神品質的詞嗎?
以“人格”來定位先知的精神品質,不是對人類歷史具有本質洞觀與深邃洞鑒的人是無法想出這樣一個詞來的。當然,這裡所謂的“人格”早已超出了一般純粹道德意義上的那種含義,它指向了一種更為深廣與本質的精神與力量,它能夠改變人類現有的精神狀況並能改換人類舊有歷史的精神面貌,甚而,這一“人格”的存在竟是宇宙包括其中所有生命賴以存在的精魂。因而,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曾認為這種人格還具有一種“神秘性”的力量。湯因比對“人格”這一概念的分析與論述比較細緻。在他看來,具有這類人格的人才是人類文明興衰成長的真正推動者與“精神”種子的攜帶者:“這些少見的超人的靈魂是一種新的特殊的性格,他們打破了原始人類社會生活的惡性週期,重新開始了創造性的工作,只有這種靈魂才是人格。只有通過人格的內部發展,個別的人才能夠在行為的場所的範圍外進行那些創造性的行為,進一步造成人類社會的生長。”
事實上,再也沒有比以數量的方式來解釋人類精神歷史發展的奧秘更為荒唐可笑的論調了。在自然界當中,恰恰只有人類是唯一一種不能完全以一對一的方式來論優劣的生命體。
在那篇舊文中,我曾根據“宇宙人格”這一概念又延伸出個體和社會兩種人格,這三種人格就構成了對眾生不同人格的一種簡單歸類。
所謂個體人格,就是我們一般的凡俗大眾所具有的精神氣質與品格狀態。之所以稱之為個體人格,乃是我們在生活中總會以“自我”為中心,我們的精神品質與行為表現總是潛藏著一個為己的“小我”,只有當我們滿足了的自身的需求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後,我們才有可能想起他人,想起一些比我們自身的生存更為偉大的價值與意義。一般而言,我們的這種精神展現只能如午夜微弱的螢光,不要說照亮別人,它甚至無法照亮自己前進的方向。有時,我們有可能具有某一更高一級的社會或宇宙人格的行為與舉動,但那只是一些不連貫的行為片段和精神煙花,它根本無法形成一個恒定的、具有影響力的生命性的畫面。一般所謂的世界偉人可稱得上是具有“社會人格”的人。在個體人格的基礎上,他們的人格精神在“行為的場所”(社會)中,已越過個體性的“自我”界限與範圍而擴展到人類的某一社會或歷史階段之中,並對其形成一定的影響與推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這些人格力量成為該社會或歷史階段的精神的推動者與改變者。但是,當這種人格離開了被稱之為“社會”或“歷史”等特定的概念與維度之後,則其精神品質所建立的豐功偉績很快就灰飛煙滅了。時空的經緯已將其分割與撕裂成顯得並不那麼偉大的瑣碎點滴。甚而,因更多不可告人的隱私與陰謀,這些所謂具有“社會人格”的人只不過是一些令人不齒甚至遺臭萬年的惡棍流氓。
正如湯因比所言,只有那種宇宙性的人格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人格,他們的精神維度是宇宙的、永恆的。這些精神因數彌散在宇宙中,會點燃與照亮整個宇宙,宇宙因之而充滿了靈氣與生命,它們如果交織在人類的歷史與文化中,則會化為一曲曲對造物主神聖而永恆的讚頌樂章。雖然,他們的人格精神中無疑仍具有前兩種人格狀態,但其宇宙人格已將其融貫為一個整體,繼而使它們從本質上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當然,這種改變並不僅僅是宇宙人格者自身所具有的那些特殊的精神質素,就像湯因比所言,更重要是他們擁有前兩種人格所不具備的那種“神秘性”。在天啟宗教中,則使用了一個簡潔明瞭的名稱來稱呼這些人,即他們就是被造物主所揀選以向世人傳達永恆的信仰與真理的先知。
二
對伊斯蘭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宇宙人格的剖析,不需要去列數他一生中那些改變整個世界精神面貌與人類文明圖景的業績,僅在其生活的海洋中掬一朵浪花就足以說明一切。一滴水珠足以顯映出一個世界。
不知誰說過,也許它早已成為經典名言:要想識別一個人,你最好在兩種情況下去觀察與審視他的反應與表現:春風得意、功成名就之時;失意落魄、四面楚歌那一刻。
就我身患惡疾的經歷與閱讀聖傳的感受而言,自己好像更多地是從先知的後一種境況中找到了自己人生得以慰藉的精神食糧。聖傳就是這樣,不管你是怎樣的一個人,身處人生的哪個階段,哪一階層,正遭遇著怎樣的痛苦與折磨……你都可以從其中找到相對於你的那種類似境遇,然後你自然也會看到先知穆罕默德有著怎樣的人格表現。這就是造物主使先知成為人類社會最底層的一名成員——孤兒的哲理,因為從孤兒到人類世界最偉大的先知,其間要經過多少艱難與坎坷以及不同身份的轉換,因此,社會中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總會在先知身上找到自己所熟悉的身影。我自認為自己是那種深感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的人,如此灰色的人生感受卻最終讓我在聖傳中找到了對自己人生沒有任何理由不樂觀豁達的答案,甚而,它讓我無以辯解,無地自容。
當然,這一點並不僅僅和我自身的生活境遇有關,它好像也是所有人對自己生活的一個慣常看法與感受,在生活中它總是在影響著我們對自己周圍世界的人和事的認識與態度。
的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為不幸的人,也都感到自己所遭受到的痛苦與磨難要比他人多得多。朋友來找你訴說他的痛苦,你會一邊嘴上應付與安慰著,一邊卻在內心中憤憤不平:你那點“輕傷”算什麼!與此相反,我們又總認為所有的人比自己生活的都更幸福、更快樂,尤其像先知那樣的人物,正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知!那是什麼人!我們豈能與他相比?
這種認識會給我們帶來一種錯覺,以為先知是真主所特慈與佑助的人;主所佑助的人,還有辦不成的事兒,完不成的事業嗎?主所喜愛與誇讚的人,還有什麼不如意的?一主之下,眾生之上,何等的榮耀,何等的崇高。
顯然,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如果沒有正確的認識與超然的心態,很有可能會因無法接受或忍受來自真主的考驗而背離主道甚至譴怒於主。
幸好主的創造與宇宙的常道並非如此,相反,它恰在這裡和我們的常識認識有了本質性的區別,正如先知穆罕默德自己所說,一個人的品級和他所遭受的磨難成正比。如果說先知穆罕默德具有凡人所無法企及的那種宇宙人格,則其所受到的痛苦與磨難的考驗比起我們又會怎樣呢?
三
在聖傳中,先知穆罕默德一生中所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可能就是塔伊夫之行了。
塔伊夫之行是反映先知穆罕默德宇宙人格的一個典型實例。在這一事件中,先知向真主的訴說和向真主所作的禱詞,可作為我們解讀其宇宙人格表現的一個“亮點”。
西元619年,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為聖的第10年,先知在麥加遭到多神教徒前所未有的迫害與打壓,被迫出走麥加去塔伊夫尋找新的希望與援助。
這一場景讓我想起了孔子周遊列國後遭奚落的那一殘酷的命運……
但就是在這樣一個孤立無援的狀況下,塔伊夫之行繼而遭到了比在麥加更為令人沮喪的結局。放下這次遭遇的經過暫且不談,僅麥加到塔伊夫90公里之遙的徒步行走,就是一趟令人難忘的艱苦旅行。筆者在巴基斯坦的時候,曾聽到有些兄弟講述過從麥加到塔伊夫徒步旅行的感受,由於道路崎嶇坎坷,至中途,行者的腳已腫脹,血泡鼓起,疼痛難忍,想起先知宣教使命之艱難,有人竟然坐在地上大哭起來……
由先知穆罕默德的義子宰德·本·哈裡斯陪同下的這此求援,仿佛從開始就已註定了它失敗的命運。由於塔伊夫與麥加之間的密切的貿易往來,塔伊夫的貴族們豈能如此輕易地丟掉自己發財的買賣,走向受苦的信仰之路。相反,為了表明自己堅定的決心,他們授意和指使那些愚人與懵懂的兒童,除了對先知進行淩辱性的奚落與挖苦外,還大打出手,投擲石塊,致使先知和宰德慌不擇路,恰躲進仇人的葡萄園中,受傷的雙腳血流不止,竟然染紅了鞋子。就在仇人的葡萄園中,先知捧起了雙手,向他的養主難過地開始了以下的訴說與祈禱:
安拉呀!我要向你訴說,我已力竭計窮,人們在欺侮我。仁慈者中最仁慈的主啊,你是弱者之主,是我的真主。你把我交給誰呢!交給這些給我難看臉色的人呢,還是把我交給我的敵人!只要你沒有對我生氣,我無所顧及。只有你能拯救我。求你保佑,不要對我發怒。責怪我吧,直到你滿意。無能無力,別無辦法,唯有依靠你了。
也許,有人會問:這就是先知所遭受的最困難的境地嗎?
比起先知以後在麥迪那的奮鬥歷程及遭遇,塔伊夫之行顯得平淡與單薄了許多,它既沒有以後先知與猶太人之間險象環生的那些驚險情節,更沒有令人膽寒的血腥的戰鬥場面,甚至,伊斯蘭的這位先知連生命都沒有受到什麼大的威脅,僅僅在這一處境所作的祈禱就能體現出先知穆罕默德的偉大的人格嗎?
的確,比起以後先知奮鬥歷程中的那些大的歷史事件而言,塔伊夫之行猶如他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但是,如果我們將塔伊夫之行放到先知穆罕默德一生宣教的軌跡與走向看,則這一事件的特殊性就凸顯出來。
如果將先知宣教的歷史看做是一條顛倒的抛物線的話,則塔伊夫之行恰處於其最底部,也就是說,塔伊夫之行是先知穆罕默德一生宣教進退維谷的最低潮時期,也是真主考驗先知偉大人格隱忍與否的臨界點。
因為,在塔伊夫事件之前,先知正面臨其人生最為悲痛的時候,這段時間被以後的穆斯林史學家稱為“悲痛之年”,之所以如此稱謂,乃是因為在這一年,先知在事業與精神上同時失去了兩位最重要的幫手與支柱;先是聖伯艾布·塔利蔔的去世,後是賢妻海蒂哲的歸主。他們的離去使先知遭到了他傳教以來從未有過的磨難與痛苦,肉體和精神同時向他一股腦的襲來,以至於“這樣的痛苦足能使性格堅強的人動搖和絕望,能使性格堅強的人悲痛欲絕,沉湎於無窮的哀思之中,而無暇再考慮其它事情。”(《穆罕默德生平》,P,149)古萊什人仿佛就在等著這一天的到來,他們總是要等著某個機會來同先知算一下總帳。當先知出門走在大路上,甚至那些一文不名的愚昧之徒竟也攔住先知,無理尋釁,朝他頭上抛灑髒物。以至於先知曾反復地說:“安拉啊,艾布·塔利蔔去世前,古萊什人還沒能這樣傷害我。”而塔伊夫事件之後,則黑暗逐漸遁去,曙光悄然來臨,兩次阿格伯盟誓,揭開了先知遷往麥迪那的序幕,從此,穆斯林將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最終迎來了徹底的勝利。如果悲痛之年是先知個人一生中遭到的最為痛苦與悲傷的時候,則塔伊夫之行則是在此基礎上雪上加霜。
非但如此,塔伊夫之行的艱難境地還在於它是一場先知近十年的精神考驗中一次最猛烈的衝擊。顯然,如果我們認為先知面臨的考驗只是其宣教後的某一階段或時期,就大錯而特錯了。實際上,當痛苦與磨難的考驗來臨之後,它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先知,也幾乎沒有中斷過。熟悉聖傳的人,不會忘記多神教徒對先知所使用的各種方式的欺侮與迫害。限於篇幅我們這裡不再一一列舉。
最後,塔伊夫之禱是先知獨自向安拉做的一個祈禱,它突出反映了先知的真實的內心世界的情感與精神狀態,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真正顯露出人的真實本質。
現在,讓我們同先知穆罕默德一起走進他的精神世界,分析一下這段禱詞所蘊含的深遠意義,同時也將他與個體和社會人格的人的行為作一比較。
四
安拉呀!我要向你訴說,我已力竭計窮,人們在欺侮我。仁慈者中最仁慈的主啊,你是弱者之主,是我的真主。
也許這就是我們將塔伊夫之行看作是先知面臨絕境的一個原因吧。在宇宙的造物主面前,先知打開了自己的心扉,說出了自己的無奈和痛苦,他已身處絕境,幾乎無路可走,想一想下面這件事,我們就會知道先知當時的處境有多糟糕。當他從塔伊夫返回麥加時,由於害怕麥加多神教徒知道他去塔伊夫求援而遭到傷害,竟然需要一個保護人的承諾保護與陪同才敢回到麥加。的確,在偉大的造物主面前,即使人類最後一位先知也呈現出作為被造物的無能與弱小,他需要造物主在其人生最艱難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以助其走出困境,擺脫麥加多神教徒的迫害與折磨。當然,既便在這種情況下,先知的人格與行為也與其他人格的精神截然地區別開來。
首先,一個人在一生中起所朝向與汲取力量的物件與精神源泉的不同決定了其精神與人格的潛質與高度。顯然,先知在其一生中,無論順逆榮辱,其內心中永遠都有一個不變的精神朝向,那就是永遠只以造物主的喜悅與惱怒來作為其價值取向與行為導向的行止標準,這一點,在其生命中沒有瞬間的改變與遲疑。作為個體或社會人格的人而言,總不免要將生命中患得患失的事物投向了和他們一樣的被造物上,其生活中的喜怒哀樂也總免不了受到它們的影響與牽制,至於拋棄一切投向造物主的懷抱,有時候幾乎是與投向絕望與死路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只有在世界上找不到可找的援助與幫手的時候,我們才找到了安拉,朝向了他。
另外,先知與其它兩種人格所陷入絕境的性質有著本質的區別,先知從來不會因為失去世俗的利益而感到有什麼惋惜與難過的,更不會為爭奪它們而去浪費自己寶貴的生命。他的一生只是為了其偉大使命的完成。熟悉聖傳的讀者都知道,為了使先知能夠停止宣教,古萊什的貴族和首領們曾這樣對先知承諾過:“如果你想要金錢,我們大家斂錢給你,使你成為我們中最富有的人。如果你想要榮譽地位,我們讓你做我們的首領。你不在場我不決定任何事情。如果你想做國王,我們讓你做我們的國王。”面對這些誘人的承諾,在歷史中除了先知,還能有什麼人對此無動於衷的呢?也許,先知對自己伯父的回答,可以看作是對所有上述一切的回答:“即使他們將太陽放到的我的右手,把月亮放在我的左手,我也絕不放棄自己的事業,要麼我以身殉教,要麼它借真主的援助而獲得成功。”因而,所謂先知所遭到的絕境,從來不是緣於私己的利益與享樂,它只是為了讓整個人類能沐浴在正信的恩澤之中,從而獲得永恆的幸福與快樂。
而作為平凡的個體,每個人所遭受到的許多苦難與所處絕境的因素,莫不是由於自己的欲望與私念所致,即使那些具有社會人格的人,雖然其人生的追求也許最初的動機是偉大而崇高的,但我們發現,當這些信誓旦旦的誓言或理想的光環消失的時候,他們仍逃不出唯我獨尊的利己宿命。三者之間精神境界的差別,何止天地之遙。
你把我交給誰呢!交給這些給我難看臉色的人呢,還是把我交給我的敵人!
乍一看到這句話,我們眼前可能會一亮,多麼熟悉的言詞與語氣。於是我們好像終於找到了一種替自己辯解的藉口,哈,先知也會做這樣的“嘟啊宜”(祈禱)嘛!俗話說,人是泥捏成的,誰還沒有個土性。這不,先知也有忍耐不住,對安拉進行抱怨與訴苦的時候,“你把我們給誰呢?交給這些給我那看臉色的人呢,還是把我交給我的敵人!”
的確,大凡在信仰生活中走過一段路的人,在遭遇屬於自己的絕境時,也許就會擁有類似或更多的這種言詞上的怨氣與訴說。“主啊!你為什麼這樣對我?”“我不偷,也不搶,還禮拜封齋,何以要我遭此磨難?不拜你者,作奸犯罪者,他們卻酒肉穿腸過,滿臉紅光存!”“主啊!公道何在!天理何在!”不用再往下列數我們自己再熟悉不過的那些控訴了。也許所謂個體人格的人就是如此,他們永遠走不出“自我”的牢籠,哪還有遨遊九霄的境界?至於那些社會人格,在同樣的遭遇面前,好像有了更高的超出個體人格的堅忍與耐力,但終究這種所謂的高尚人格仍未脫離憤憤不平的怨氣與私恨,甚而會將其作為日後變本加厲地去復仇雪恨的籌碼。所謂“頭懸樑錐刺股”、“臥薪嚐膽”等好像早已讓我們忘掉了其背後那些不光彩的動機。不管怎樣,我們總是想為自己的這種作法找到一個恰當的藉口:宇宙人格的先知不是也會如此嗎?真是這樣嗎?那麼,讓我們往下看吧。
只要你沒有對我生氣,我無所顧及。只有你能拯救我。求你保佑,不要對我發怒。責怪我吧直到你滿意。
因這段禱詞我們才看到了上段禱詞非但不是一種不滿的控訴,相反,它恰是先知向宇宙的造物主展現其在絕境中決心與意志的言詞,是啊,對於先知而言,宣教的使命就是其生命的全部價值和意義,是他的一切。曾幾何時,當來自安拉的啟示出現了暫時性的中斷,先知以為安拉拋棄了自己而不再下降啟示時,他甚至因無法獲得啟示而焦慮和失望,以至於想跳下懸崖……。如今,他又怎能因為安拉對自己的這種考驗而心懷不忿與怨恨呢?
與此同時,這段禱詞不但讓我們對前面先知的那一訴說和所謂的“控訴”有了釋疑性的答案,而且又呈現出一種新的讓我們無法理解與想像的精神高度:“求你保佑,不要對我發怒。責怪我吧直到你滿意。”
顯然,這一點的確讓個體人格者無法理解。如果說,我們在生活中出現了罪錯,則這種懺悔性的祈禱無疑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須的,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所說,先知所處的境遇的原因,不但不是自己個人的錯誤或罪惡造成的,甚而,我們可以斗膽地說,它恰恰是由於真主委派給先知的使命所造成的,由此,何來懺悔與自責。的確,精神境界的距離隔斷了我們與先知之間在的溝通與交流。“小我”與“無我”的精神境界也隔絕了真正的理解的可能性。
這裡,先知的禱詞又一次讓我們跌入了不解的困惑當中……
但是,如果考慮到先知由於其聖品所具有的特殊性,則這種理解的張力也許會有所鬆弛。
顯然,由於先知們擁有超越於個體人格的那種聖品特質,因而,在一般人看來的正常或正當行為,也許在先知那裡就有可能構成了罪錯。諸如先知努哈對其當時的不信者的詛咒性的祈禱,易蔔拉欣的三次“謊言”,穆薩的誤殺,也許對一個平常的人而言,根本不算什麼,因為這些作法本來就是一種理所當然或無法避免的事情,但對先知而言,竟成了他們在後世無顏見主以替世人求情的原因。
也許這些可以作為我們對先知穆罕默德的這段禱詞理解的一個起點。
在先知看來,自己的宣教事業走到這個地步,就是沒有完成真主交給自己的任務,就是自己對宇宙造物主的的疏忽和怠慢。作為人類最後一位先知,他從來不會考慮到自己應該向偉大的造物主抱怨和要求些什麼。就像他對眾生的那種品行一樣,無論是他的家屬、親人、朋友、弟子,甚至是那些冒犯他,對他傷害甚至想要殺害他的人。就從造物主與被造物的本質關係看,罪責與缺憾永遠是在被造物那一邊,讚頌與超絕,清淨與無染永遠只歸於造物主。顯然,僅僅從“存在”的“無中生有”這一點看,人類對造物主豈有不讚頌與敬拜之說,可以這樣說,這種“創造”的恩典是作為信仰者的一個基本認識,遑論先知。這裡,伊斯蘭與其它宗教尤其是那些世俗主義者的信仰與宇宙認識論有著明顯地差別。在伊斯蘭當中沒有所謂的神正論問題,因為人從其本質上講,根本就沒有可以對造物主加以質問與控訴的前提與籌碼(當然,這並非表明人不能對這一問題給予一定的研究和探索)。
無能無力,別無辦法,唯有依靠你了。
至此,先知的境界昇華到了其精神境界的最高處,而這一段言詞也是宇宙與人類歷史存在的核心動力與根本基礎。無獨有偶,作為一名聖徒,馬明心竟然也將這段話作為了伊斯蘭信仰的終極言詞,他曾這樣不無穿透力地說:“伊斯蘭的終點,那是無計無力!”
但是,先知在這種處境下的這一表白更顯示出特殊的含義,它仿佛是對自己所作禱詞的一個總結,這一總結直接將上述禱詞的意義貫穿起來,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信仰認識體系與一個神聖而無限的精神高度,就是在這一認知角度,我們才真正瞭解了先知為何能夠有如此的訴說與禱告,“無能無力,別無辦法,只靠你了”,這段禱詞揭示了造物主與與一切存在之間的本質關係,也就是說,無論宇宙的存在還是人類的歷史,與其說是一種外在的表像規律不如說是來自安拉的直接創造與意志的維護。一切動力與力量的源泉只來自造物主。因此,作為一個弱小而卑微的人而言,還有什麼可以作為依持的呢?
在這種認識中,先知的那種“無我”的胸懷和認識境界就凸現出來,因此,對他在這一處境之中所表現出的那種精神狀態我們仿佛也能夠給予理解了。
就是在這一點上,沒有極限的宇宙人格境界才得以真正體現,由於這一點境界直接伸向的存在的核心——造物主。所以,在先知的一生中,無論是其處於絕境之中,還是在勝利時刻,其意義與價值的指向也都指向的造物主,這就是當先知從絕境中走出來時,他並沒有這因對這一處境所受到的曾對其加以打擊與傷害而遷怒於他的敵人,就像他在其勝利的時刻從來不趾高氣揚地向眾生證明什麼。
實際上,塔伊夫事件之後還有一個插曲,它恰恰能夠作為我們論述先知偉大人格的一個驗證性的總結,歷史仿佛有著屬於它自己的設計和安排,這種設計和安排恰恰是歷史的常道,即使唯物主義者也不得不相信它是驗證歷史的唯一標準那樣。顯然,歷史或者說安拉意志的安排,它要在歷史的舞臺上正面地驗證先知人格,那就是,在脫離絕境或者說在突然遭逢“轉敗為勝”的一個契機時,一個人在能夠對其仇人或給其製造使其陷入絕境的人的給予報復或復仇的時候,他又會怎樣做呢?
據布哈裡聖訓的傳述,由於看到先知的這種痛苦與磨難,真主派遣加百列和管理山嶽的天使,來到先知的跟前告訴他,如果他願意的話,天使們可以將麥加這個山谷夷為平地,就在這種情況下,先知說:“我願意這座山谷的人最後走向正道。”
與此相對,當先知攻克麥加,在眾人的簇擁下走進麥加時,他沒有表現出如社會人格的那種慣常行為,他既沒有振臂高呼和煽情作秀,也沒有以不可一世地姿態去搜尋著他的仇敵以待日後算帳,他只是垂下了他那高貴的頭顱,以至於額頭觸到了駝鞍上,並接連不斷贊念與感謝真主,就像我們在聖傳中看到的那樣,當那些欲置於其死地的仇人被帶到他跟前時,他最後只是對他們說:“去吧,你們都自由了!”
“當真主的援助和勝利降臨 , 而你看見眾人成群結隊地崇奉真主的宗教時,你應當讚頌你的主超絕萬物,並且向他求饒,他確是至宥的。”(110:1—3)
“當你的事務完畢時,你應當勤勞,你應當向你的主懇求。”(94:7—8)
這就是來自天啟訊息的教導,來自造物主的囑託。
當然,作為具有宇宙人格的先知,他做到了安拉所命令他的一切,他也完成了安拉所交給他的任務。先知的任務和個體、社會人格的本質不同在於,他不僅僅只是在傳達使命,實際上,在一生傳達的過程中,恰是他對其使命的忠實的踐行。
也許,這就是伊斯蘭為什麼將“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當作其核心信仰的一個必然組成部分。這裡,我們毋須贅言,因為這一句話已揭示了伊斯蘭的信仰與其精神的所有向度和所有方面,作為人類最後一位先知,作為一個具有宇宙人格的先知,穆罕默德將一直受到來自眾天使和信士們的祝福,甚至來自造物主的誇讚,而這一點已說明了一切:“真主的確憐憫先知,他的天神們的確為他祝福。信士們啊!你們應當為他祝福,應當祝他平安!”(3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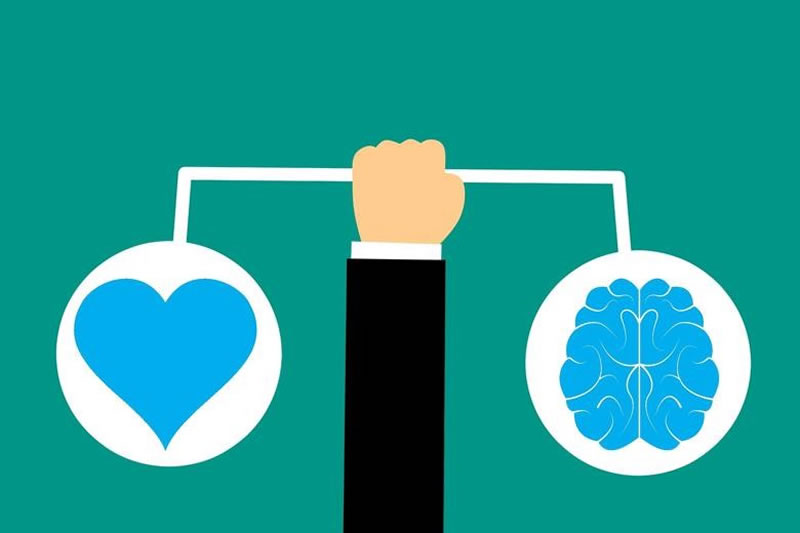


1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