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所處的這個物質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還要保有人文氣息的話,
那它就不能忽略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的期許。
我們的過往不可以像月球上的鐵礦床一樣,
僅僅只是被功利地當作一種滿足我們自身好奇心的工具。
——馬歇爾·霍奇森
馬歇爾·霍奇森
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逐漸發展壯大,以及西方國家在干涉中東事務上遭遇的挫折,物質技術高度發達的西方各國啟動宣傳機器,把中東混亂的根源歸結到曾經輝煌燦爛的伊斯蘭文明本身,在廣大民眾之中引發了極其不利於文化交流與溝通的「伊斯蘭恐懼症」。
由是,伊斯蘭(沒有「教」)日益成為一個阻礙時代發展的「落後宗教」,由於她不像基督教那樣經歷過改革,便成為了「束縛人性」「極端、不人道」的代名詞。
著名的學者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W. Said)曾經寫下《報導伊斯蘭》以及《東方主義》等極富批判性的鴻篇巨著來揭露西方政治家們的「良苦用心」,並講述了西方話語對人們的思維與認知所造成的危害。毫無疑問,這些著作確實促使人們從一個新的角度去思考當今世界的局勢。
實際上,早在愛德華·賽義德成名以前,西方的許多學者們就試圖跳出傳統的西方中心視角,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給人們呈現出一個真實的世界,書寫整體的世界史,對不同的區域文化進行比較研究,不再把西方當作例外,從而消除廣大民眾對這些地區的誤解。
馬歇爾·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更是在這些學者中獨樹一幟。他不把伊斯蘭當成西方學科分類中的「宗教」,而是搜集亞非歐共生圈(Afro-Eurasia)各地的有關伊斯蘭的材料,讓「伊斯蘭世界」變成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整體,並對該整體進行系統的跨學科研究。
可惜的是,由於其觀點過於非主流而鮮為人知。在如今這個伊斯蘭日益成為焦點,而人們卻對伊斯蘭的誤解加深的時代裡,重新審視霍奇森及其著作有了更多的現實意義。
霍奇森的生平
1922年4月11日,霍奇森出生於印第安那州的里士滿,在基督教貴格教派的文化氛圍中長大,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後來他進入芝加哥大學的歷史系進行學習。除了必修的歷史課程之外,他本人主要的興趣點便在於伊斯蘭世界。
霍奇森1955年的博士論文《阿薩辛派:早期伊斯瑪儀派支系尼紮裡派與伊斯蘭世界的鬥爭》糾正了時人很多關於伊斯瑪儀派的錯誤觀點。同時在寫作的過程中,他也積累了大量有關伊斯蘭世界的知識,而他對伊斯蘭世界的嚮往也日益強烈,並萌生了去遊學的想法。
考慮到當時的歷史系還沒有一部講述伊斯蘭世界史的過硬的教材,霍奇森從1956年開始思考相關方面的著作,以滿足教學的需要。他向大學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交了申請,但是他的專案卻沒有獲得通過。不過,作為補償,基金會撥給了他遊學的資金,支援他在伊斯蘭國家進行為期半年的考察研究。
不久,他便前往北非、中東地區遊學,結識了對他日後的學術思想有深刻影響的天主教傳教士福柯等人。後來,他又輾轉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對當地的伊斯蘭團體進行考察。
回國後,他一方面開始籌備書寫關於伊斯蘭世界史的教科書,另一方面設計了講述「伊斯蘭文明史」的課程大綱,正式投入到教育工作當中。自然,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博士論文導師古魯伯。
古魯伯的巨著《中世紀的伊斯蘭》(小編特地在此省了「教」字)基於阿拉伯語的文獻去解讀伊斯蘭的發展史,並突出強調了伊斯蘭文明的普世性,以及與其相配套的伊斯蘭式的人道主義。
在古魯伯以及其他學者的幫助下,霍奇森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歷史教材《伊斯蘭的冒險:在一個全人類文明中的良心與歷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然而,在完成最後的修訂之前,霍奇森於1968年6月10日便與世長辭了,起因是中暑,因為在芝加哥炎熱的夏季裡,他依然去參加馬拉松賽跑。
作為一個虔誠的貴格派信徒,霍奇森的生活十分規律、有節制,同時他本人還是一個素食主義者。
學者的自我修養
和賽義德一樣,霍奇森一生致力於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與否定,並一樣地學識淵博、寬容和善。和賽義德不同的是,霍奇森的著作沒有令人熱血沸騰的譴責,相反,他的文字像是溫柔的文學作品,在一點一滴地陳述著不為人所知的歷史知識與文化現象。
就歷史研究的方法而言,霍奇森是實證主義的,這意味著他並不刻意讓自己遵從任何一個學科或者是理論,而是進行跨越學科似的思維跳躍,其最終目的在於還原所描述的地區的歷史真實。在歷史觀上,他更加強調的是文化的作用,把文化作為人類產生進步的過程以及儲存其意義的寶庫來研究,反對當時西方學界所強調的「物質-技術主義」(technicalism),即把物質技術的進步作為衡量文明優越性的唯一標準。
在霍奇森看來,一個學者最重要的品質,在於持之以恆的自我審查。他做出這種論斷基於兩種認識:首先,學術研究並非在先驗的意義上就是公正無私的;其次,學術本身就源自具體的文化偏見,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這種文化偏見。也就是說,每個學者的三觀都深受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不可避免地有這樣或那樣的「偏見」。
因此,唯一的做法就是在不斷地交流與溝通之中反思自己的知與行,並始終把人文關懷放在首位,以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方法書寫歷史。
然而,他也因此陷入到了自己所設的困境之中。由於他不停的自我反思以及堅持實證的做法,使得他不敢就學科上的重大問題作出自己的論斷,這就喪失了構建自己的學科話語的能力。
此外,由於批判自己所處的體制,他在書寫歷史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去運用本身已經存在的老舊的敘述方式。雖然他在書寫的時候力圖嚴謹,但是因為沒有強而有力的觀點而沒有受到更多的重視,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其去世後,他的著作鮮為人知,也不受重視。
《伊斯蘭的冒險》
霍奇森沒有把伊斯蘭僅僅只當做一個宗教來進行研究,而是將它作為一個對人類歷史進程有重大貢獻的文明來研究。
《伊斯蘭的冒險》第一卷
全書分為六個部分,一共有三卷。第一卷《古典時代的伊斯蘭世界》,包含了一個很長的敘述部分。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對「伊斯蘭」這一概念進行的分析。
為此,除了原來就有的「伊斯蘭教的」(Islamic),他還創造了幾個術語:Islamdom,可以翻譯為「伊斯蘭世界」,或者是「伊斯蘭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地區」,即在這個地區人們用伊斯蘭的價值觀念進行思考,或者實施管理,類似阿拉伯語中的دار الاسلام,即統治者使用伊斯蘭法進行管理的地方;還有Islamicate,可以翻譯成「伊斯蘭式的」,或者是「具有伊斯蘭特徵的」(可以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歐美的」「英倫風的」「歐美風的」「西方式的」進行對比)。
Islamicate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且這個文化概念和「伊斯蘭的生活規範(即所謂的「教」)」( الدين الاسلام)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它指的是一種源自作為生活規範(即「教」)的伊斯蘭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包括審美等),人們在它的影響下投入到現實的工作與生活中,並創造出相應的文化產品,但這些文化產品和信仰生活卻沒有必然的聯繫。
因此,Islamic是對於完全接受伊斯蘭的人——即穆斯林——而言的,而Islamicate是對於所有人而言的,只要他或她根據或借鑒伊斯蘭的一些價值觀念以及文化現象(不是全部)進行自己的創作,那麼就可以說他或她所做的就是「伊斯蘭式的」「伊斯蘭風的」(Islamicate),無論他或她是猶太人,還是基督徒,抑或是漢族人。
另外,該卷講了自先知穆罕默德到伍麥葉王朝時期的社會、經濟、法律、文化等,再現了伊斯蘭文明的形成。
第二卷《伊斯蘭世界的中期擴張》,講述了伊斯蘭世界性文明的建立和蒙古的入侵。雖然哈裡發權威不再,伊斯蘭的生活規範也分支眾多(如遜尼與什葉),但是作為文化的伊斯蘭傳播範圍很廣,從波士尼亞到孟加拉灣、從摩洛哥到印尼的廣大地區,其中更多的人接受了伊斯蘭的生活規範(伊斯蘭教),也有更多的地區實施伊斯蘭的統治(Islamdom),當然,更多的人也借鑒伊斯蘭的文化價值觀念以及審美方式(Islamicate)。
第三卷《火藥帝國與現代時期》講了伊斯蘭世界「波斯式的重構」,標誌就是以薩法維為首,奧斯曼、帖木兒(莫臥兒)為輔的伊斯蘭世界體系的建立。對於霍奇森而言,薩法維才是伊斯蘭文化的中心,而奧斯曼以及帖木兒只是該文化體系的邊緣。
借助著波斯語言及政治理論和文化實踐的廣泛傳播,伊斯蘭世界的繁榮達到了頂峰,也在全球享有著文化霸權的地位,西方的大航海以及殖民擴張,都沒有能夠撼動伊斯蘭世界的霸權。最後到了十八世紀,由於西方從農業經濟轉變到了工業經濟,從而實現了超越,伊斯蘭世界雖然依舊在發展,但是由於速度趕不上西方而最終「衰落」。
伊斯蘭世界的文化霸權
霍奇森去世的時候,該書的最後一卷還沒有修訂完成。他的同事魯本·史密斯則無私地幫助他完成了最後的編輯工作,直到這本書被艾德蒙·伯克三世所賞識並出版。在聲明裡,史密斯反復指出他是在「準確無誤地」對「只屬於」霍奇森的著作進行編輯。
結語
無論是賽義德,還是霍奇森,他們一生中念念不忘的就是打破西方政治家的話語權,做一個獨立於體系之外的人文主義學者,提醒世人不要被話語權所操控,而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對於霍奇森而言,世界歷史和伊斯蘭文化的發展史已經變得難以分開。一些學者認為,他把伊斯蘭放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點(但是他本人曾說中國的南宋時期可以被看作是一場工業革命,只是由於蒙古人的到來而被終止),通過對伊斯蘭歷史的「人道的」「人文的」解讀來實現其道德價值,即促進世界不同文化群體的交流與溝通,宣傳普世的人文精神,而這也是伊斯蘭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對於信仰,絕無強迫,因為是非已經分明)。
在霍奇森及其追隨者看來,曾經「神聖」的西方不再享有特殊性,它僅僅只是亞非歐共生圈中的一個小小的角落。人類的歷史是由整個共生圈的各個民族來書寫的,西方是一個參與者,但是並非主導者。
《艾布·達伍德聖訓集》當中有這麼一個故事:阿伊莎因為駱駝不聽話而生氣,先知對她說:「事物若失去了溫和,就會變得醜陋」(健全聖訓)。也許霍奇森本人也曾經對這段話細細地加以品讀,知道即便他自己身處西方,也不希望世界上的是與非都用西方的價值標準來衡量吧。
每個文明都有她自己的特徵,也有自己的自我完善之路。也許人們能做的,就是不斷地交流與溝通,相互幫助,增進相互之間的理解吧。
【今日主筆 \ 徐偉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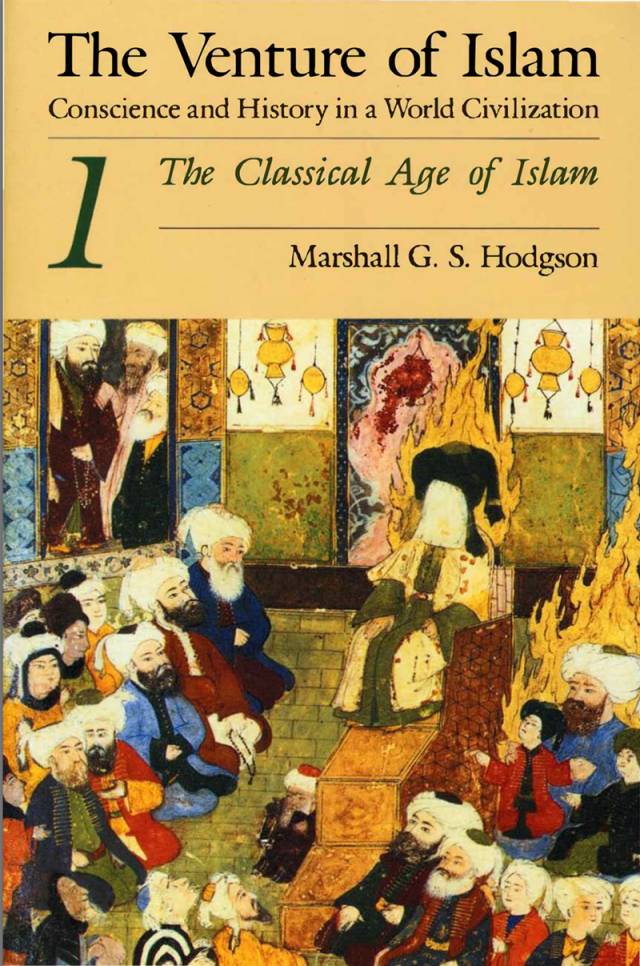



1條評論